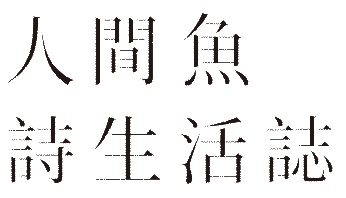詩人的歲月.詩人的背影
專訪 蘇紹連
線上訪談 | PS.黃觀
文字編輯 | 周賢
攝影 | 郭潔渝
文字編輯 | 周賢
攝影 | 郭潔渝
詩,就是生活,它是我的骨血
黃:您的詩有幾個特質,讀起來有音律感,朗讀會有一種節奏;還有一個特質就是,不難讀,幾乎什麼都可以入詩。請問,對您來說,詩是什麼?
丁:我以前寫過一首詩叫〈不寫詩我會死〉,大致上是說,寫詩是我很重要,記錄生活的日記。這樣一個紀錄,成為我某種程度的自我療癒。有些年輕詩人會說,詩怎麼可能療癒人,不要賦予詩這麼大的療癒的功能。但實際上,詩對我而言,已經不只是療癒,對我而言是宣洩。曾經有人問過我,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覺得,我跟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我看這個世界每天都很火大,如果我不發洩,它會影響我的生活和工作,詩可以負擔我每天情緒的宣洩與療癒。
倒過來看代表我很愛這個世界,因為每一件我看到的事,都很在乎。我一直認為,愛恨是糾纏的兩面,它是一個螺旋。最斷絕的分手叫做形同陌路,把對方當作空氣,我沒辦法這樣看待這世界。我每天看待這世界,是愛恨交織,所以必須要寫,有時候二行、三行,有時候就是長長的一首,大概二十多年了吧,我的日記就是詩。
至於朗讀的節奏感,我寫每一首詩,都有一個反覆以聲音讀誦的過程,不同題材、不同形式的詩作應該有不同的聲音地景,因此對我而言,除了純粹訴諸視覺的詩之外,我對於每一首自己的詩,都會反覆操練詩裡的音樂性,尤其是內在的音樂性,那種節奏感同時也是詩的一部分。
黃:您的詩有幾個特質,讀起來有音律感,朗讀會有一種節奏;還有一個特質就是,不難讀,幾乎什麼都可以入詩。請問,對您來說,詩是什麼?
丁:我以前寫過一首詩叫〈不寫詩我會死〉,大致上是說,寫詩是我很重要,記錄生活的日記。這樣一個紀錄,成為我某種程度的自我療癒。有些年輕詩人會說,詩怎麼可能療癒人,不要賦予詩這麼大的療癒的功能。但實際上,詩對我而言,已經不只是療癒,對我而言是宣洩。曾經有人問過我,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覺得,我跟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我看這個世界每天都很火大,如果我不發洩,它會影響我的生活和工作,詩可以負擔我每天情緒的宣洩與療癒。
倒過來看代表我很愛這個世界,因為每一件我看到的事,都很在乎。我一直認為,愛恨是糾纏的兩面,它是一個螺旋。最斷絕的分手叫做形同陌路,把對方當作空氣,我沒辦法這樣看待這世界。我每天看待這世界,是愛恨交織,所以必須要寫,有時候二行、三行,有時候就是長長的一首,大概二十多年了吧,我的日記就是詩。
至於朗讀的節奏感,我寫每一首詩,都有一個反覆以聲音讀誦的過程,不同題材、不同形式的詩作應該有不同的聲音地景,因此對我而言,除了純粹訴諸視覺的詩之外,我對於每一首自己的詩,都會反覆操練詩裡的音樂性,尤其是內在的音樂性,那種節奏感同時也是詩的一部分。
詩,是對這個世界「我不知道」的回應
黃:您認為怎麼樣可以成為一個詩人?寫詩是你的日常,可是對某些人來說,不一定是這樣。
丁:我前陣子讀辛波絲卡的作品,讀她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辭,她得獎詩的標題:「詩人與世界」。她說,真正的詩人,是要不斷說:「我不知道」。她對這個世界,不斷的在說:「我不知道」,詩人每一首詩的創作,都是為了回應「我不知道」這句話。她說她在紙頁上面寫下任何一個句點,她都會猶豫,她體悟到,我寫下的這個答覆,回答「我不知道」的這個答覆,是不可能完滿的。也就是說,隨時寫下的東西是可以被摒棄的,於是詩人繼續嘗試,繼續寫下自我的不完滿,對這個世界,因為充滿著不知道,所以提出問題,繼而發展出一連串的詩作,最後成為詩人的種下的果實,而文學史家會幫詩人的詩作,用巨大的紙夾夾在一起,命名為詩人的作品全集。
這讓我很感動,因為我在寫的時候,我真的充滿著「不知道」,我對這個世界滿是質疑。我用詩回應對世界的質疑,對自己不完滿的質疑,一直不斷的寫,是再次、反覆的證明這個質疑確實存在的,而且繼續的不完滿,不完滿變成驅動我寫詩的力量。
我覺得真正的詩人,他必須不斷的說「我不知道」,而且必須不斷的面對自己永恆存在的匱缺,然後去填補這個匱缺,最後才發覺無法填補,好自虐啊,而那又是一種享受。
辛波絲卡的話語,讓我想到中國古代的蘇東坡,他總是在對抗這個世界的不完滿。他用一種哲學性的方式在詩詞中告訴你,也無風雨也無晴。告訴我們,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要起舞弄清影。可是你有沒有發覺,他接下來的生命歷程,一樣心情不好,一樣經常喝酒,一樣會因為自己身心的痛苦,藉由詩、詞、文宣洩各種「不知道」。但是,他每次都在這樣的自問自答當中,留下許多生命自我療癒的餘音。
對他而言,那樣的回應,最終還是證明了這個世界永遠不存在完滿,所以他不斷在尋找完滿的可能。他常常說不在乎,那個不在乎其實是對自己當下不完滿的一種回應,是療癒,他其實非常在乎。
簡單來說,詩人跟小說家、散文家不一樣,他不斷的要像辛波絲卡說的,我不知道,我要去反叛這個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去面對這個世界,要不斷的自我質疑,甚至要質疑這個世界,詩人應該是永遠的反叛者。
|
長詩就是王道,當台灣成為長詩的國度,
台灣就是華語詩在華文的世界文學上最精彩的地方。 黃:以現在詩的入門門檻,還有現在的風潮,包括到下一個世代,為什麼您認為長詩是王道?為什麼您還是寫長詩?長詩在詩的方面,佔了什麼樣的地位? 丁:中國古典詩人,在隋唐之後,除了律詩、絕句等近體詩的書寫外,有另外一個精彩的展現,就是古體詩的寫作,古體詩相對於近體篇幅更長。西方非常多知名的詩人,也會有長詩作為生命的一部分與書寫的典範。對我而言,從在地通往世界的關懷、對存在價值與人類命運的思辨,在四十七歲的現在,是書寫的主軸。但丁《神曲》或其它經典,都承載了詩人的哲學思考與存在價值之內省,也涉入了相對等的知識性或者說是博物學,這樣的內涵不是三、五行能夠完整寫出來的,必須就由長詩的書寫才能完成。 我對自己有一個非常大的期許和期待,我認為長詩才是王道。因為當台灣有一天成為長詩的國度,台灣就是華文文學世界裡,現代詩書寫能夠表現得最精彩的所在,這也才能被稱之於詩歌復興或詩歌盛世。 |
寫出前所未有的詩,延續華文傳統,帶來一種現代的革新。
黃:您這一次選擇這個長詩的創作《荒城》,要用現代詩的末日書寫。什麼是末日書寫?
丁: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末日書寫的小說,一個虛構的區域碰到一場現實的災難,譬如說核災、地震,譬如說疫情,人們會怎麼面對?古往今來很多作家,都在處理這樣的命題,表面上是從實走到虛,但其實它比實更實。因為這會涉及到我們怎麼去思考人性的各種層面,在即將面對末日的時候,人類的存續關鍵又是什麼?正因為現在尚毋需面對,所以我們更好奇這些問題,更想透過自身的想像,去思考人們面對災難的時候,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小說家不斷在書寫,但詩人呢?
這三、五年,我一直都透過田野踏查的方式書寫島嶼。我從歷史上去找台北,從空間上去找高雄、苗栗、找台灣各地,這都是屬「實」的。在這些踏查的過程中,看到許多的崩毀敗壞,於這座島嶼不斷地反覆循環。一旦崩毀敗壞,累積到無法收拾的局面的時候,我們能不能用一首詩,表達詩人對於未來這種「不知道」的回應?
這是《荒城》的起點。《荒城》與《編年台北》同時開始書寫,只是《荒城》是斷斷續續地寫,但也因為這個斷斷續續,加上碰到疫情,所以我對於《荒城》的思考……
黃:您這一次選擇這個長詩的創作《荒城》,要用現代詩的末日書寫。什麼是末日書寫?
丁: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末日書寫的小說,一個虛構的區域碰到一場現實的災難,譬如說核災、地震,譬如說疫情,人們會怎麼面對?古往今來很多作家,都在處理這樣的命題,表面上是從實走到虛,但其實它比實更實。因為這會涉及到我們怎麼去思考人性的各種層面,在即將面對末日的時候,人類的存續關鍵又是什麼?正因為現在尚毋需面對,所以我們更好奇這些問題,更想透過自身的想像,去思考人們面對災難的時候,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小說家不斷在書寫,但詩人呢?
這三、五年,我一直都透過田野踏查的方式書寫島嶼。我從歷史上去找台北,從空間上去找高雄、苗栗、找台灣各地,這都是屬「實」的。在這些踏查的過程中,看到許多的崩毀敗壞,於這座島嶼不斷地反覆循環。一旦崩毀敗壞,累積到無法收拾的局面的時候,我們能不能用一首詩,表達詩人對於未來這種「不知道」的回應?
這是《荒城》的起點。《荒城》與《編年台北》同時開始書寫,只是《荒城》是斷斷續續地寫,但也因為這個斷斷續續,加上碰到疫情,所以我對於《荒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