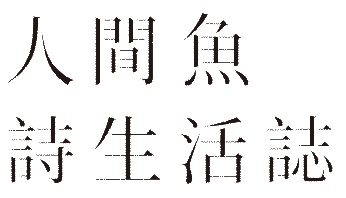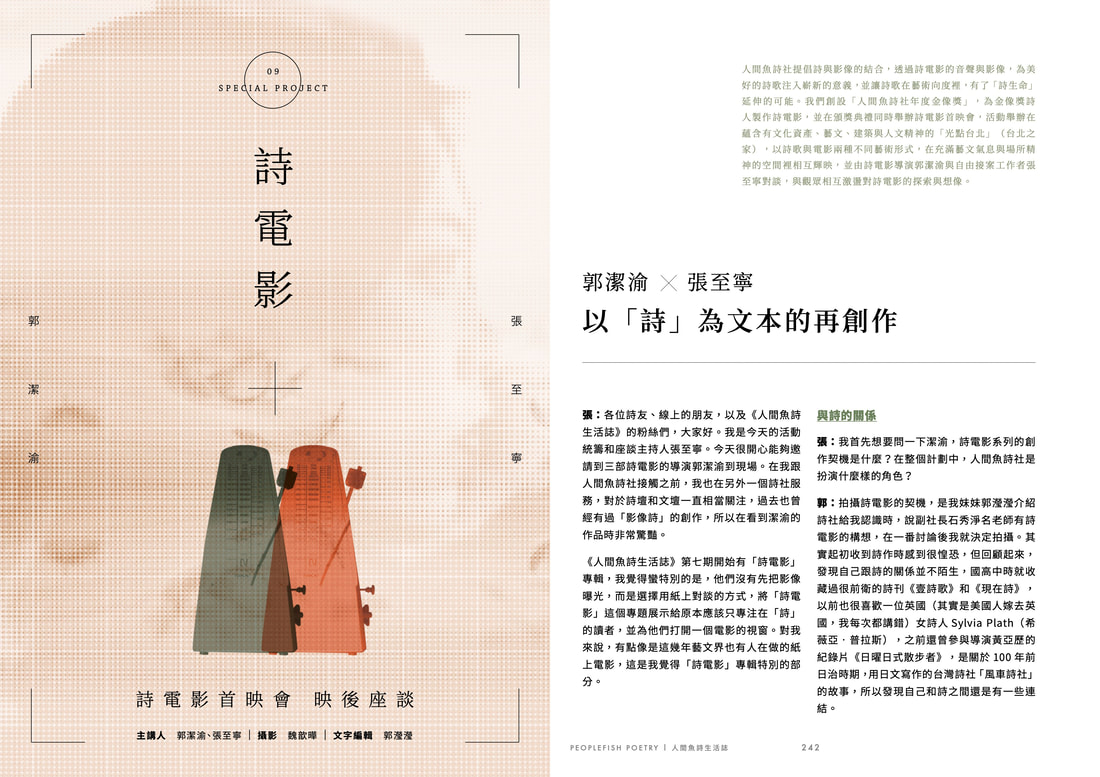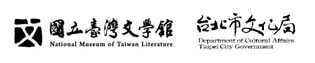詩電影首映會 映後座談
人間魚詩社提倡詩與影像的結合,透過詩電影的音聲與影像,為美好的詩歌注入嶄新的意義,並讓詩歌在藝術向度裡,有了「詩生命」延伸的可能。我們創設「人間魚詩社年度金像獎」,為金像獎詩人製作詩電影,並在頒獎典禮同時舉辦詩電影首映會,活動舉辦在蘊含有文化資產、藝文、建築與人文精神的「光點台北」(台北之家),以詩歌與電影兩種不同藝術形式,在充滿藝文氣息與場所精神的空間裡相互輝映,並由詩電影導演郭潔渝與自由接案工作者張至寧對談,與觀眾相互激盪對詩電影的探索與想像。
郭潔渝 X 張至寧:以「詩」為文本的再創作
什麼是「詩電影」?
張:「影像詩」或者我們說「詩電影」,有些人形容是意識的,或是抽象的、是非線性敘事的,其實經過時間的沉澱再看,往往都會給看的人很多新的感受。石秀淨名老師在第七期詩生活誌提到,他想引出「詩電影」這個概念,這是我一開始接觸人間魚詩社時很好奇的,因為以往很多跟詩有關的影像就叫「影像詩」,也有段時間很常用「微電影」這個詞,或者是再更早一點,短片只能出現在影展、公視或一些獨立的影像廣告裡,並且會被歸類在實驗電影。我想知道「詩電影」作為一個新時代新篇章的定義詞彙,你怎麼找出它與上述這些舉例的互異跟共質性。
郭:我比較不會在意「詩電影」被稱呼為什麼,當然這會是一個大家很好奇的事。大學時,我在金馬影展看過一部改編自法國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詩作的影片,那部影片不是很有順序的敘事,而是有點破碎的,有點像我拍的詩電影。比較特別的是,它很像powerpoint,畫面是一些底色、色塊,比如說紅色變成綠色,再變成白色、黃色、黑色這樣,然後這樣一直變、緩慢的變。它的詩句(因為是法文我看不懂,但是我猜它應該是詩句)會是白色的,從右跑到左、從左跑到右,就這樣一直跑,我印象中應該是有人聲在唸詩吧。我會想要問大家,大家覺得這個是詩電影嗎?如果大家覺得這樣不是詩電影的請舉手。
(現場沈默)
郭:那我換個方式問,假設我今天放映游鍫良老師的〈權術〉,結果畫面是全黑的,只有聲音,大家會覺得這樣是詩電影嗎?
(《人間魚詩生活誌》發行人許麗玲、現場觀眾舉手參與討論)
許:有可能是,因為我覺得黑色跟聲音之間的對比跟張力,也可能是一個很棒的創作。
觀眾A:我認為作品出來,導演就死了。所以我覺得東西拍出來以後,觀看者覺得什麼,就是什麼。
郭:沒錯。那我再問一個,如果詩電影只有畫面,沒有人、沒有聲音呢?大家覺得這樣可以嗎?
觀眾A:我曾經有看過一部電影,也是在影展時候看的。整部電影,它講的語言我聽不懂,從頭到尾就是一隻船,從右邊開到左邊,很大的一個鏡頭,從頭到尾就只有這樣。是詩電影嗎?是啊。
郭:是。所以什麼都可以是,什麼都可以不是,這是建立在我們自己心中的,所以要去定義詩電影的話,我自己是覺得有一點困難,不過,雖然我知道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但我還是做一個「什麼都有的」比較安全,因為詩電影的文本是詩人的原作,我會考量到,當一般觀眾或讀者想要觀看一個叫「詩電影」的影片時,會想要觀看到什麼?換成是我的話,我應該還是會希望聽到有人在讀這首詩,因為詩特別的地方,是除了文字之外,也有各種去讀它的方式。
詩裡的「聲音」
剛才胡淑娟老師的同學朗讀詩的方式,就是一種方式,而澤榆的朗讀也是一種方式,不管你用什麼方式去朗讀它,那都是你詮釋的方式。在我對詩這種語言的想像裡,「聲音」是很重要的。當然它也可以是很視覺畫面的,比如說把字排列成圖形狀的詩,不過一般來講,不管是中文詩或是西洋詩,詩的唸法每個人各有不同,所以我拍詩電影時,一定會把聲音朗讀考量進來。而每一首詩給我的感覺不一樣,比如說石秀淨名老師的〈大見解〉,在初次讀時,很多段落在我腦裡會直接產生朗讀的聲音,有些是用怒吼的,有些是竊竊私語,或是詩裡面有一些括弧裡的字句,我看到的時候就覺得它是氣音,就是這種很直觀的感受。如果回到剛剛至寧說的詩電影「定義」方式,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定義,也許我們再拍更久、拍更遠,就會開始有「什麼是詩電影」,「什麼是微電影」的約定俗成,或是哪一種比較像「影像詩」。
張:你的意思是,詩電影其實是一個主觀感受,而不是作為一種載體被定義?
郭:我目前的感受是這樣。我們如果說要拍詩電影,也可以拿起手機就拍,每個人的方式不同。
張:剛才我們討論到法國導演的影片,讓我想到賈曼的《藍》,畫面是全藍的,整部片是全藍的,只有賈曼一個人在講話。
(「年度金像獎詩人」評審孟樊舉手參與討論)
孟:對,賈曼的那部片,螢幕上就是一片藍,因為賈曼後期已經失明了,這其實也是他自己切身的反應,畫面從頭就是藍的,藍到整段時間都是藍的,他用旁白講他自己的創作、他的人生、他的感想,雖然不是用詩的語言來說,可是從某個角度來講的話,這部電影裡,導演談他的創作、他的人生,其實也有詩電影的感覺,所以如果把詩電影再擴充來說,也不見得旁白或是裡面的聲音就是詩的語句,是不是?如果是主持人講到的這一部《藍》,大家怎麼看?
張:對,非常感動,我覺得我們心有靈犀。剛才馬上想到這個作品,因為它的文字就是非常的詩意,所以當視覺跟人聲、文字內容中的「詩性」達成一致的時候,在觀看上面,或許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詩電影。也許我們可以很直觀的看到,「這是劇情片」、「這是詩電影」,我們可以期待那一天。
剛才胡淑娟老師的同學朗讀詩的方式,就是一種方式,而澤榆的朗讀也是一種方式,不管你用什麼方式去朗讀它,那都是你詮釋的方式。在我對詩這種語言的想像裡,「聲音」是很重要的。當然它也可以是很視覺畫面的,比如說把字排列成圖形狀的詩,不過一般來講,不管是中文詩或是西洋詩,詩的唸法每個人各有不同,所以我拍詩電影時,一定會把聲音朗讀考量進來。而每一首詩給我的感覺不一樣,比如說石秀淨名老師的〈大見解〉,在初次讀時,很多段落在我腦裡會直接產生朗讀的聲音,有些是用怒吼的,有些是竊竊私語,或是詩裡面有一些括弧裡的字句,我看到的時候就覺得它是氣音,就是這種很直觀的感受。如果回到剛剛至寧說的詩電影「定義」方式,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定義,也許我們再拍更久、拍更遠,就會開始有「什麼是詩電影」,「什麼是微電影」的約定俗成,或是哪一種比較像「影像詩」。
張:你的意思是,詩電影其實是一個主觀感受,而不是作為一種載體被定義?
郭:我目前的感受是這樣。我們如果說要拍詩電影,也可以拿起手機就拍,每個人的方式不同。
張:剛才我們討論到法國導演的影片,讓我想到賈曼的《藍》,畫面是全藍的,整部片是全藍的,只有賈曼一個人在講話。
(「年度金像獎詩人」評審孟樊舉手參與討論)
孟:對,賈曼的那部片,螢幕上就是一片藍,因為賈曼後期已經失明了,這其實也是他自己切身的反應,畫面從頭就是藍的,藍到整段時間都是藍的,他用旁白講他自己的創作、他的人生、他的感想,雖然不是用詩的語言來說,可是從某個角度來講的話,這部電影裡,導演談他的創作、他的人生,其實也有詩電影的感覺,所以如果把詩電影再擴充來說,也不見得旁白或是裡面的聲音就是詩的語句,是不是?如果是主持人講到的這一部《藍》,大家怎麼看?
張:對,非常感動,我覺得我們心有靈犀。剛才馬上想到這個作品,因為它的文字就是非常的詩意,所以當視覺跟人聲、文字內容中的「詩性」達成一致的時候,在觀看上面,或許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詩電影。也許我們可以很直觀的看到,「這是劇情片」、「這是詩電影」,我們可以期待那一天。
郭:剛才有提到,「聲音不一定要是詩句」,其實這一次我有做類似的事情,只是可能還不夠大膽。在《大見解》裡面,有些時候是有字幕,有些時候有人在講話,或是都沒有(但沒有字幕),那是因為在講話的聲音其實是朗讀詩句,只是詩句並不是按照石秀淨名老師原本在詩裡呈現的位置,有些時候甚至是有點破哏,提前出現。
張:有去疊合或混音的感覺。
郭:對,那時候有試圖想要做,但是因為這不只是我自己的創作,我認為還是要回到詩裡面去,因此就沒有像剛才說的,放進別的不在詩作裡的東西,不過也許以後可以偷偷放進來。
張:有去疊合或混音的感覺。
郭:對,那時候有試圖想要做,但是因為這不只是我自己的創作,我認為還是要回到詩裡面去,因此就沒有像剛才說的,放進別的不在詩作裡的東西,不過也許以後可以偷偷放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