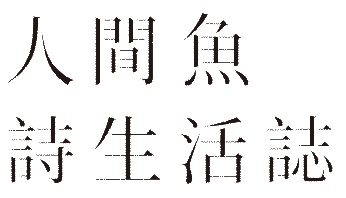迴避思想與邏輯——北園克衛其人其詩
田原評詩.日本詩選
文|田原
20世紀20年代,引領日本現代主義詩歌的詩人屈指可數,北園克衛便是其中一位。
北園克衛(Kitazono Katsue,1902-1978),生於日本三重縣伊勢市的朝熊町,本名橋本健吉(初期的筆名為亞坂健吉)。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學部。1923年經詩人生田春月的推舉在《文章俱樂部》雜誌上發表處女作。進入昭和時代後,陸續在《文藝耽美》、《VOU》等雜誌發表詩歌和短篇小說。1927年,與翻譯家、詩人上田敏雄等一起創刊《薔薇.魔術.學說》雜誌。翌年,與西脅順三郎、瀧口修造等詩人聯合創辦超現實主義機關雜誌《衣裳的太陽》,並與詩人上田敏雄、上田保共同撰寫「在日本的超現實主義宣言」,成為日本超現實主義詩人先驅之一。從1928年起,開始使用現在的筆名。1929年6月,處女詩集《白色影集》由厚生閣書店出版。這部詩集被稱為「迴避思想與邏輯,追求感覺世界裡的純粹性,是日本現代詩初期的現代主義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成果」,可以說是北園克衛詩歌實驗的出發點。他正是由於這部詩集確立了他的創作方向。1930年,成為《LE SURREALISME INTERNATIONAL》詩誌的同人。次年與岩本修藏一起創刊《白紙》詩誌。1932年,詩誌《白紙》改名為《MADAMEBLANCHE》。同年8月,詩集《年輕的殖民地》出版。之後,相繼出版有詩集《圓錐詩集》(1933年)、《夏天的信函》(1937年),後者的詩風更具有明朗的性質,被伊藤信吉稱為是「該時期北園克衛的代表詩集」、「明朗的智性抒情像透明的玻璃一樣鮮明」。《火的紫羅蘭》(1939年)也被伊藤信吉稱為是「在抒情美和嶄新性中,以及在感性和智性的交織中,為讀者提供了至高無上的平衡」。除此之外,還出版有《堅硬的雞蛋》(1941年)、《黑火》(1951年)、《藍色距離》(1958年)、《煙的直線》(1959年)、《眼鏡中的幽靈》(1965年)、《空氣的箱子》(1966年)、《白色斷片》(1973年)等30餘部詩集,以及評論集《天的手套》(1933年)、《鄉土詩論》 (1944年)等5部,並翻譯出版有法國詩人馬拉美的詩集《戀歌》(1934年)、拉迪蓋的詩集《火的臉頰》(1953年)等3部。同時還出版有短篇小說集《黑色邀請函》等。
芳賀秀次郎在評價北園克衛的作品時,曾寫過這樣一段話:「北園克衛的詩歌技巧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日語語法中助詞的用法。本來助詞在日語中的作用,是接續在體言(漢語中的名詞和指示代詞—--筆者加註)、用言(漢語中的形容詞和動詞—--筆者加注)和助動詞後面,表示這個詞與其他詞之間的關係,或者添加一定的意義。但是,北園克衛卻讓刻板的名詞放鬆下來,並想要賦予助詞一個使命—--打開自由且帶有意外性的局面。詩歌在有限的表現中,沒有必要無條件地遵從合理的語法常規。不是為了語言和語法而表現,語法正是為了表現而存在的。這裡一定有北園克衛的冒險和一個發現以及他探索的喜悅。」
北園稱自己的詩分為抒情、和風、實驗三種,詩的傾向涉及多方面。鄉土詩群的抒情性較為明顯,和風調的詩群帶有俳句的韻味,其中類似「實驗性」的前衛詩群,比起語言的意義更重視詩行的排列和文字的形狀,一行一語的詩,拼湊成圖形各異的詩等,對形狀和圖案傾注獨特的視線,獲得了有趣的成果。詩人自身在1953年出版的詩集《黃色橢圓》中,題為「我在詩歌中的實驗」一文裡做過如下的描述:「1927年,我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影響,發現了一個〈場〉,在此之前我雖然用好幾種形式創作了多少帶有獨自性的詩歌作品,但是那些詩某種意義上,混合有別人的成分。我自身的詩作品第一次獲得全方位的成功時的喜悅至今仍記憶猶新。那是來自純粹創造的愉悅和滿足。我記得幾乎是在半年間,用這種新發現的詩歌形式,連續創作了很多作品……(中略)像用刷子在嶄新的畫布上繪畫一樣,在稿紙上單純地選擇意象鮮明的文字,創作像保羅.克利的繪畫一樣簡潔的詩歌。就是說無視語言帶有的一般性的內容和必然性,即把語言作為色、線和點的象徵來使用。這就是我的詩歌實驗原理。」
正如北園自己所言,在他的詩歌寫作生涯中,其大部分詩作皆以極簡主義的語言表現法為自己描摹著作為詩人的自畫像,這一點確實跟超現實主義畫家保羅.克利運用點、線、色和獨特的想像構成的藝術語言有相似之處:簡單中透出深遠和神秘、平易中凸顯出內在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從而確立有別於他人的詩歌符號。某種意義上,語言如同北園的巫術,更像他吟誦的禱文,在帶有強烈個人化的節奏感中,通過自己與眾不同的直覺感受奇思遐想地建構風格迥異的詩歌王國。我曾在圖書館偶然看到過北園克衛同樣在1953年翻譯出版的法國英年早逝的詩人、作家雷蒙德.拉迪蓋的詩集《火的臉頰》。這本詩集由曾浪跡中國(上海)和歐洲多年、跟魯迅在上海有過交往的藝術家宇留河泰呂(漢語名為潘·宇留河)裝幀設計,黑色封面上,裡紅外白的折紙造型彷彿定格了一個視覺觀念,像雕塑又酷似靜止的火焰,抽象又具體,很難說清畫面的具象所指和由此衍生出的意義,但過目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