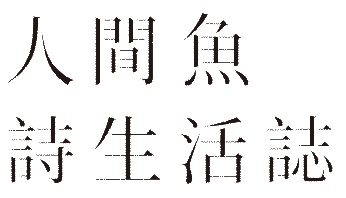數位麵包馬戲團
愛/人間/KOLAS
文|KOLAS YOTAKA
一位西元一世紀末的羅馬詩人尤維納爾(Juvenal)寫過這首諷刺詩:
⋯⋯很久以前,從我們把選票賣給任何人的時候起,
人民已經放棄了我們的責任,
對於曾經擁有軍事指揮權、高級文官、軍團⋯⋯等一切的人民來說,
現在,焦急地希望只有兩件事:麵包和馬戲團⋯⋯
「麵包和馬戲團」(或麵包和遊戲)(拉丁文:panem et circenses)是古羅馬的現象,指政客不談政策,只向貧窮的羅馬人提供小麥(麵包)與昂貴的馬戲表演作為娛樂,以麻醉選民。以現代的話來說,即透過民粹主義的手段,獲取政治權力。
詩作發表於二千年前的羅馬,批判的不只是統治者,而是人民。人們追求的再也不是與生俱來的政治自由,所剩下唯一的關心,就是等待政府配糧救濟,沉迷於不用大腦思考的娛樂(如:羅馬競技場上的血腥人獸大戰)。詩人批判羅馬人自行讓渡了公民義務,隨波逐流,寧願追隨任何民粹政治領袖,以滿足他們腐朽的慾望。這種年代,政策不重要,理念不重要,價值不重要;快速、直接、膚淺、低俗、謾罵、血腥殘殺的娛樂讓選民看了痛快,政客剛好可藉此分散民眾注意力,腐化人心,反正只要風向對了,先贏了再說。
馬戲團
人還是人,從一世紀走到二十一世紀,我們畢竟還是人。綜觀二千多年來,儘管科技進步,但人性卻不斷歷史重演。舉世皆然。
當今的競技場,已從橢圓形的血腥肉搏戰場,轉移到網路社群與媒體。只要人手一機,人人可觀賽,且成本低廉,沒有代價。你可表明身份,甚至可隨時匿名參戰,當參戰的成本越來越低廉,人就越來越多,在場邊(手機前)激情叫囂「殺死他!」「幹掉他!」「除掉他!」的群眾不斷聚集。這也意味著理性、冷靜、正直、坦白的空間越來越少。原本的自由人(Freemen)被誇大又充滿娛樂感的政治議題分散注意力,自由人已不自由,喪失思考能力,無法(也不願)分辨資訊的真與假,於是再度淪為可輕易被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或金錢)動員的奴隸。
你大可自以為識途老馬地說,台灣啊,總有政客操控議題,絕對有中國介選才造成如此結果⋯⋯云云。當然,這些都是既存事實,但這不是我今天想討論的範疇,畢竟怪別人很容易,說自己是受害者最方便。今天想請大家跟我一同自我反省:我們是否自甘墮落,只想直接看答案。相較於挖掘真相,我們更喜歡一看就懂的梗圖、誇大的資訊、仇恨的短片。我們正不斷透過鍵盤,集體養出一群可怕的政治動物,而這一群動物,有的正在競技場內廝殺,有的正在場邊叫囂,他們正藉著數位科技,不斷鼓吹粗俗與平庸,讚美盲目與無知,打擊理性與冷靜,摧毀人性與尊嚴。我們非但沒有阻止,還繼續鼓勵著,如今病情已更加惡化。
你或許不同意,會反駁我,並說「這才是真民主!」「直接民主!」越是笨拙、醜陋、憤怒的指控或表現,越被認為是「真」。但現在請您低頭仔細看看手機,點選任何一個新聞入口網站,瀏覽幾個新聞標題,事實證明,社群媒體越發達,「重複性」的負面攻擊就越猛烈。這些「新聞」是真是假?還是抄來抄去?恐怕連你都沒把握。許多新聞以看似真實的片段作為基礎,卻加以橫向發展,加油添醋扭曲事實,打擊當事人的信用。因此在媒體、社群中的所見所聞,若非提高音量的嘲諷,就是充滿挑釁地污辱對手,且有錢就可以買廣告重複播放假新聞。我們正不自覺地允許高強度、高重複的仇恨洗我們腦。以為這種政治結合媒體的套路,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當今最高明的政治。
例如,我們剛剛經歷一場爭取國家統治權的數位競技。現在最流行的戰技,不外乎就是利用社群媒體揭人瘡疤、挖人隱私、曝人緋聞、拆人違建,舉凡P圖、打卡、手板、甚至幼稚到嘲弄對手的姓名亂取綽號、大呼小叫⋯⋯高潮不斷。當我們被洗腦到心神耗弱,開始相信這一切就是政治的常態,殺戮才正要展開。
殺戮的手法包括哪些?二千年前戰士血腥廝殺,只有戰士下場,觀眾在場邊看。如今觀眾不只在場邊叫囂互相傳遞憤怒,還被鼓勵一起下場:先「標籤」鎖定對手,分享誇大扭曲的新聞以醜化、定罪、污名政敵;然後透過演算法與金錢,購買網軍、業配新聞、買按讚數和點閱數,形成「風向」;最後在強風中以「道德」之名點燃怒火,鼓動追隨者乘風一轟而起,快速降落數位競技場中央,用手機向政治上的對手展開社會性屠殺,直到對手社會性死亡。
據統計,目前全國使用社群網路的人口高達93.2%,社群排行前三名為LINE、FACEBOOK、與Instagram。根據臉書發布的訊息,2023年全台灣的臉書用戶數已突破2100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90%。在社群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上網,匿名不但讓人享有戴面具的自由,也助長「一言堂」,毫無尺度的發言攻擊,讓人產生顛覆威權、打破階級的錯覺。更糟的是,網攻經常夾雜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不講別人,就講我好了。對我最常見的攻擊,就是拿我的名字「Kolas」消遣,稱為我「狗拉屎」「谷拉死」,或將我父親的名字Yotaka故意音譯成日文的「夜鶯(即「妓女」之意)」。光是一個非漢人的名字,就足以發動一場鋪張的攻擊,更不要說「疫苗」、「衛生紙」、「違建」、「論文」、「緋聞」、「黑金」、「核食」、「萊豬」、「國籍」、「同婚」、「廢死」?
馬戲團內有團長:即法西斯主義者、極權主義者。從一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其共同的特質,就是大量利用民粹,壓制反對意見。到了二十一世紀,當政治加上科技,失去思考能力的人民,聯手養出更可怕的數位法西斯怪獸。我們那些數位法西斯,隱身在鍵盤背後,進行專制統治,展開毫無尺度的權力遊戲。但當我們不自覺反被法西斯煽動,以為可以在仇恨中顛覆既有的權威,創造新英雄,以為這是真民主。但有沒有可能,我們也在陰溝裡翻船,離「真民主」越來越遠?
麵包
「民主」的「真」諦,是「真實的資訊」與「思考的人民」。我想跟大家一起檢視的,不是掌權者、不是特定政黨、不是政客、也不是當然存在的中國介選⋯⋯而是我們自己。我們還是那具有思考能力的「自由人」嗎?或者我們已成為人云亦云的暴民?我們是否充滿憤怒與不滿,動輒以「讚」「怒」「哈」「哇」在場邊發洩,謊稱自己代表的是多數人,是「真民主」?我們是否遠離了真正的公共政策,耽溺於過度的娛樂?
例一:
從來沒有搏鬥訓練的立委,在立院演出全武行時,大多踉蹌扭捏,一點也不美。但因擔心選民若沒有看到自己在電視上潑咖啡灑麵粉丟內臟,會被認為「沒有作為」、「沒有看到人」;所以不得不放下手邊的法案和預算書,稱是為了更崇高的理念,不得不生硬地吼兩下、踢兩腳,像憤怒的孩子般大聲喊叫,「為民喉舌」。然後,等著有人按讚。反之,就怕沒有讚。
例二:
清晨必須孤單地站在大馬路邊的肥皂箱上,僅管來來往往的車流人群大多只管忙著上班,候選人笑僵了臉,也必須在冷空氣中上下來回鞠躬拜託,活像裝上了電池的電子玩具,展現苦行謙遜的能耐,證明自己可為民服務。車流與人流看在眼裡不禁嘴角暗笑,享受這片刻顛覆權威的求饒片段。政治人物心甘情願,彎腰拱手,等著有人為這場苦肉計按讚。反之,就怕沒有讚。
例三:
就算不是基督徒,也要硬撐陪選民過聖誕節;就算不是佛教徒,也需不斷參加法會;就算再沒有錢,也一定要在路邊懸掛修圖修到認不出本尊的選舉看板。不論平日問政有多麽認真,就算與親家或喪家有沒有關聯,一但被傳「我娶媳婦她沒到」「我阿嬤告別式他沒來」⋯⋯就掛了。更別說有些選區還有選民期待「沒買票就不投」。是我們,把病態變成常態。丑角們,也只能盡全力討觀眾歡心,荒廢了原本應盡的義務不說,為了「讚」,連自己都不認得自己。
政客、選民,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能不能,透過理性、民主的教育,成為真正的自由人,選出真冠軍?其實我們可以決定,要看怎樣的表演,要選出怎樣的冠軍。選民的素質與養成,決定我們配得怎樣的政治。
當我們取回思考的能力,就能修正政治人物的日常作息、影響各家新聞台的人力分配、調整觀眾收看電視的頻率、刺激經濟活動的機制,影響民主教育的品質、定義日常娛樂的類型。更進一步,我們將可棄絕販賣恐懼的樂趣,抵制仇恨動員的商機。
總是希望還有愛
詩人奧登(W. H. Auden)曾於1939年出版一首詩〈法律像愛情(Law Like Love)〉,開頭便寫道:
法律,園丁說,就像太陽。
法律是主宰,世上的園丁都要服從,
不論明日、昨日、今日⋯⋯
奧登使用諸多隱喻,解讀「法律」,詩一開頭即道出,「法律」就像太陽,園丁的生命,被太陽定義:太陽決定了園丁生活的規律。正如法律主宰了一切。這位1907年出生的英裔美籍詩人,反法西斯、反極權、反希特勒,在此指涉的法律,顯然是「政治」的結果。奧登對於政客們總是以人為手段操控法律與道德,感到強烈不安。膚淺的政治,是殘害人性的毒藥。儘管我們對法律缺乏了解,且充滿偏見,我們總是屈服於有限的個人經驗,做出違反人性的行為。正如我們對「愛」也一無所知。
總是希望,還有愛,在政治中亦然。
⋯⋯很久以前,從我們把選票賣給任何人的時候起,
人民已經放棄了我們的責任,
對於曾經擁有軍事指揮權、高級文官、軍團⋯⋯等一切的人民來說,
現在,焦急地希望只有兩件事:麵包和馬戲團⋯⋯
「麵包和馬戲團」(或麵包和遊戲)(拉丁文:panem et circenses)是古羅馬的現象,指政客不談政策,只向貧窮的羅馬人提供小麥(麵包)與昂貴的馬戲表演作為娛樂,以麻醉選民。以現代的話來說,即透過民粹主義的手段,獲取政治權力。
詩作發表於二千年前的羅馬,批判的不只是統治者,而是人民。人們追求的再也不是與生俱來的政治自由,所剩下唯一的關心,就是等待政府配糧救濟,沉迷於不用大腦思考的娛樂(如:羅馬競技場上的血腥人獸大戰)。詩人批判羅馬人自行讓渡了公民義務,隨波逐流,寧願追隨任何民粹政治領袖,以滿足他們腐朽的慾望。這種年代,政策不重要,理念不重要,價值不重要;快速、直接、膚淺、低俗、謾罵、血腥殘殺的娛樂讓選民看了痛快,政客剛好可藉此分散民眾注意力,腐化人心,反正只要風向對了,先贏了再說。
馬戲團
人還是人,從一世紀走到二十一世紀,我們畢竟還是人。綜觀二千多年來,儘管科技進步,但人性卻不斷歷史重演。舉世皆然。
當今的競技場,已從橢圓形的血腥肉搏戰場,轉移到網路社群與媒體。只要人手一機,人人可觀賽,且成本低廉,沒有代價。你可表明身份,甚至可隨時匿名參戰,當參戰的成本越來越低廉,人就越來越多,在場邊(手機前)激情叫囂「殺死他!」「幹掉他!」「除掉他!」的群眾不斷聚集。這也意味著理性、冷靜、正直、坦白的空間越來越少。原本的自由人(Freemen)被誇大又充滿娛樂感的政治議題分散注意力,自由人已不自由,喪失思考能力,無法(也不願)分辨資訊的真與假,於是再度淪為可輕易被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或金錢)動員的奴隸。
你大可自以為識途老馬地說,台灣啊,總有政客操控議題,絕對有中國介選才造成如此結果⋯⋯云云。當然,這些都是既存事實,但這不是我今天想討論的範疇,畢竟怪別人很容易,說自己是受害者最方便。今天想請大家跟我一同自我反省:我們是否自甘墮落,只想直接看答案。相較於挖掘真相,我們更喜歡一看就懂的梗圖、誇大的資訊、仇恨的短片。我們正不斷透過鍵盤,集體養出一群可怕的政治動物,而這一群動物,有的正在競技場內廝殺,有的正在場邊叫囂,他們正藉著數位科技,不斷鼓吹粗俗與平庸,讚美盲目與無知,打擊理性與冷靜,摧毀人性與尊嚴。我們非但沒有阻止,還繼續鼓勵著,如今病情已更加惡化。
你或許不同意,會反駁我,並說「這才是真民主!」「直接民主!」越是笨拙、醜陋、憤怒的指控或表現,越被認為是「真」。但現在請您低頭仔細看看手機,點選任何一個新聞入口網站,瀏覽幾個新聞標題,事實證明,社群媒體越發達,「重複性」的負面攻擊就越猛烈。這些「新聞」是真是假?還是抄來抄去?恐怕連你都沒把握。許多新聞以看似真實的片段作為基礎,卻加以橫向發展,加油添醋扭曲事實,打擊當事人的信用。因此在媒體、社群中的所見所聞,若非提高音量的嘲諷,就是充滿挑釁地污辱對手,且有錢就可以買廣告重複播放假新聞。我們正不自覺地允許高強度、高重複的仇恨洗我們腦。以為這種政治結合媒體的套路,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當今最高明的政治。
例如,我們剛剛經歷一場爭取國家統治權的數位競技。現在最流行的戰技,不外乎就是利用社群媒體揭人瘡疤、挖人隱私、曝人緋聞、拆人違建,舉凡P圖、打卡、手板、甚至幼稚到嘲弄對手的姓名亂取綽號、大呼小叫⋯⋯高潮不斷。當我們被洗腦到心神耗弱,開始相信這一切就是政治的常態,殺戮才正要展開。
殺戮的手法包括哪些?二千年前戰士血腥廝殺,只有戰士下場,觀眾在場邊看。如今觀眾不只在場邊叫囂互相傳遞憤怒,還被鼓勵一起下場:先「標籤」鎖定對手,分享誇大扭曲的新聞以醜化、定罪、污名政敵;然後透過演算法與金錢,購買網軍、業配新聞、買按讚數和點閱數,形成「風向」;最後在強風中以「道德」之名點燃怒火,鼓動追隨者乘風一轟而起,快速降落數位競技場中央,用手機向政治上的對手展開社會性屠殺,直到對手社會性死亡。
據統計,目前全國使用社群網路的人口高達93.2%,社群排行前三名為LINE、FACEBOOK、與Instagram。根據臉書發布的訊息,2023年全台灣的臉書用戶數已突破2100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90%。在社群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上網,匿名不但讓人享有戴面具的自由,也助長「一言堂」,毫無尺度的發言攻擊,讓人產生顛覆威權、打破階級的錯覺。更糟的是,網攻經常夾雜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不講別人,就講我好了。對我最常見的攻擊,就是拿我的名字「Kolas」消遣,稱為我「狗拉屎」「谷拉死」,或將我父親的名字Yotaka故意音譯成日文的「夜鶯(即「妓女」之意)」。光是一個非漢人的名字,就足以發動一場鋪張的攻擊,更不要說「疫苗」、「衛生紙」、「違建」、「論文」、「緋聞」、「黑金」、「核食」、「萊豬」、「國籍」、「同婚」、「廢死」?
馬戲團內有團長:即法西斯主義者、極權主義者。從一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其共同的特質,就是大量利用民粹,壓制反對意見。到了二十一世紀,當政治加上科技,失去思考能力的人民,聯手養出更可怕的數位法西斯怪獸。我們那些數位法西斯,隱身在鍵盤背後,進行專制統治,展開毫無尺度的權力遊戲。但當我們不自覺反被法西斯煽動,以為可以在仇恨中顛覆既有的權威,創造新英雄,以為這是真民主。但有沒有可能,我們也在陰溝裡翻船,離「真民主」越來越遠?
麵包
「民主」的「真」諦,是「真實的資訊」與「思考的人民」。我想跟大家一起檢視的,不是掌權者、不是特定政黨、不是政客、也不是當然存在的中國介選⋯⋯而是我們自己。我們還是那具有思考能力的「自由人」嗎?或者我們已成為人云亦云的暴民?我們是否充滿憤怒與不滿,動輒以「讚」「怒」「哈」「哇」在場邊發洩,謊稱自己代表的是多數人,是「真民主」?我們是否遠離了真正的公共政策,耽溺於過度的娛樂?
例一:
從來沒有搏鬥訓練的立委,在立院演出全武行時,大多踉蹌扭捏,一點也不美。但因擔心選民若沒有看到自己在電視上潑咖啡灑麵粉丟內臟,會被認為「沒有作為」、「沒有看到人」;所以不得不放下手邊的法案和預算書,稱是為了更崇高的理念,不得不生硬地吼兩下、踢兩腳,像憤怒的孩子般大聲喊叫,「為民喉舌」。然後,等著有人按讚。反之,就怕沒有讚。
例二:
清晨必須孤單地站在大馬路邊的肥皂箱上,僅管來來往往的車流人群大多只管忙著上班,候選人笑僵了臉,也必須在冷空氣中上下來回鞠躬拜託,活像裝上了電池的電子玩具,展現苦行謙遜的能耐,證明自己可為民服務。車流與人流看在眼裡不禁嘴角暗笑,享受這片刻顛覆權威的求饒片段。政治人物心甘情願,彎腰拱手,等著有人為這場苦肉計按讚。反之,就怕沒有讚。
例三:
就算不是基督徒,也要硬撐陪選民過聖誕節;就算不是佛教徒,也需不斷參加法會;就算再沒有錢,也一定要在路邊懸掛修圖修到認不出本尊的選舉看板。不論平日問政有多麽認真,就算與親家或喪家有沒有關聯,一但被傳「我娶媳婦她沒到」「我阿嬤告別式他沒來」⋯⋯就掛了。更別說有些選區還有選民期待「沒買票就不投」。是我們,把病態變成常態。丑角們,也只能盡全力討觀眾歡心,荒廢了原本應盡的義務不說,為了「讚」,連自己都不認得自己。
政客、選民,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能不能,透過理性、民主的教育,成為真正的自由人,選出真冠軍?其實我們可以決定,要看怎樣的表演,要選出怎樣的冠軍。選民的素質與養成,決定我們配得怎樣的政治。
當我們取回思考的能力,就能修正政治人物的日常作息、影響各家新聞台的人力分配、調整觀眾收看電視的頻率、刺激經濟活動的機制,影響民主教育的品質、定義日常娛樂的類型。更進一步,我們將可棄絕販賣恐懼的樂趣,抵制仇恨動員的商機。
總是希望還有愛
詩人奧登(W. H. Auden)曾於1939年出版一首詩〈法律像愛情(Law Like Love)〉,開頭便寫道:
法律,園丁說,就像太陽。
法律是主宰,世上的園丁都要服從,
不論明日、昨日、今日⋯⋯
奧登使用諸多隱喻,解讀「法律」,詩一開頭即道出,「法律」就像太陽,園丁的生命,被太陽定義:太陽決定了園丁生活的規律。正如法律主宰了一切。這位1907年出生的英裔美籍詩人,反法西斯、反極權、反希特勒,在此指涉的法律,顯然是「政治」的結果。奧登對於政客們總是以人為手段操控法律與道德,感到強烈不安。膚淺的政治,是殘害人性的毒藥。儘管我們對法律缺乏了解,且充滿偏見,我們總是屈服於有限的個人經驗,做出違反人性的行為。正如我們對「愛」也一無所知。
總是希望,還有愛,在政治中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