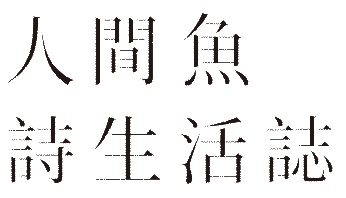人生,能否說是一場身份的鬥爭?
青世代觀點|蕭伶伃專欄
文|蕭伶伃
這個處暑到霜降,日子過得飛快。快的不是時間本身,而是將世界視為一個人的人生節奏,宛如漩渦,球體上一個一個微小身影都被捲進去了。
去年2月底開打的烏俄戰爭,引發了一場自2015年牽連1900萬餘人的歐陸難民危機之後,再一次的大遷徙。眼見烏俄問題懸而未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的張力又再一次來到世界舞台上。然後,感謝網路資訊與不同立場的極力呼籲,我們開始讀到各方說法,唯一的共識是:這樣的張力與衝突一直都存在,一直都有人為此流血。然後,加薩走廊變成人間煉獄,再一次的,巴勒斯坦人,又在戰火中開始邁向未明前程的遷徙。
可是,這個「為此」,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以巴問題?那烏克蘭人的遷徙,是為了烏俄嗎?在這幾年間,讀到或說是透過雲端見證各種「為此」延伸出的「戰爭」,這些爭執背後的根源是什麼?
在世界上的戰火綿延不休時,我進了電影院中觀看吉卜力工作室今年推出《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宮崎駿依照以往的邏輯,安排了一個身上駝著不明課題的角色,15歲少年真人(まひと),基於一個自己不是真的很情願的任務(尋找繼母夏子),踏上一段奇幻冒險旅程。
這段冒險路程不是第一次發生。你曾經看過不情願搬家,卻為了禁不起誘惑,不小心變成豬的父母而必須走進湯屋的千尋;也可能看過《霍爾的移動城堡》中,總是拉低帽簷走路,極力隱藏自己,因莫名受到霍爾利用(照顧),而被施下老婆婆咒語,嘗試破解而踏進城堡的蘇菲。真人、千尋、蘇菲,都只是這些故事中的一個引信,他們駝著的不明課題其實都是自己的身份漩渦。
在故事中圍繞著他們的那些角色們,也總有自己的課題,宮崎駿從不賦予一個角色真正的英雄,而是讓這些人物的困難圍繞在一個共同的命題上打轉:你了解自己的身份嗎?你喜歡嗎?如果不喜歡,你能怎麼辦呢?
而在我看來,包含在這一次《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宮崎駿在一貫半開放又正面的故事收尾中,為這共同的課題打了一道光:
「無論如何,人是無法沒有身份的。活在世上,你總會被賦予或爭取到一個身份的。」
生於一個在現代化歷程中不斷追問自己是誰的國家,宮崎駿的作品有他生於戰爭時期,極富昭和風格的故事剪裁。在世界戰火之間,遇到這部傳聞中的封筆之作,坐在影廳內,看著Roll Card不斷往上跑動之際,我腦袋在想的是,既然,我們都無法擺脫毫無身份的人生,也總焦慮於身份是否足以襯托自己的心理框架;也許,宮崎駿更進一步面向我們拋出的課題是:「我可以怎麼看待自己是誰?」
平野啟一郎在《那個男人》(原文:ある男)中,透過不同身份的錯置、掩藏、遺失,交織出每個人的人生其實都會回到自我凝視的提問。一個掩藏自己是在日朝鮮人身份的律師、一個借用他人身份,尋找到人生幸福卻意外喪命的男子、一個失去丈夫後卻發現丈夫生前的身份其實是借用的妻子,平野啟一郎透過書中律師城戶自顧自地,問出:
「如此一來,當我們愛上一個人,究竟是愛那個人的什麼呢?⋯⋯先是對眼前的這個人抱持好感,然後,愛上這個人包含他的過去。可是,如果知道了這個人的過去是別人的,那麼兩人之間的愛會該何去何從?」
人生是受限的,受限於身份。但《那個男人》中交錯的角色無論身份的真偽,卻尖銳地凸顯出感情的真實。在情感流動與人生的前進步伐中,身份是一個載體,不是生活的根源。然而,存在的不安總會反映在身份政治的問題上。所以,我們看到小至文學中一個一個人因身份而有的脫序決定;宮崎駿畫筆中的一個一個冒險。然而,我們卻在真實人生中看到因身份背後的歷史與眼前的未來,導引出更巨大的衝突,如此刻的以巴問題。
因身份政治衝突下的戰火,將一個一個生命與人生捲入漩渦中。如果我們近身凝視那些生命的特寫,無論哪一方都不忍卒睹。然而,回到撐起身份的那些歷史與共同體感,屬於誰的義憤幾乎要攔腰折斷另一方的脊椎。
去年2月底開打的烏俄戰爭,引發了一場自2015年牽連1900萬餘人的歐陸難民危機之後,再一次的大遷徙。眼見烏俄問題懸而未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的張力又再一次來到世界舞台上。然後,感謝網路資訊與不同立場的極力呼籲,我們開始讀到各方說法,唯一的共識是:這樣的張力與衝突一直都存在,一直都有人為此流血。然後,加薩走廊變成人間煉獄,再一次的,巴勒斯坦人,又在戰火中開始邁向未明前程的遷徙。
可是,這個「為此」,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以巴問題?那烏克蘭人的遷徙,是為了烏俄嗎?在這幾年間,讀到或說是透過雲端見證各種「為此」延伸出的「戰爭」,這些爭執背後的根源是什麼?
在世界上的戰火綿延不休時,我進了電影院中觀看吉卜力工作室今年推出《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宮崎駿依照以往的邏輯,安排了一個身上駝著不明課題的角色,15歲少年真人(まひと),基於一個自己不是真的很情願的任務(尋找繼母夏子),踏上一段奇幻冒險旅程。
這段冒險路程不是第一次發生。你曾經看過不情願搬家,卻為了禁不起誘惑,不小心變成豬的父母而必須走進湯屋的千尋;也可能看過《霍爾的移動城堡》中,總是拉低帽簷走路,極力隱藏自己,因莫名受到霍爾利用(照顧),而被施下老婆婆咒語,嘗試破解而踏進城堡的蘇菲。真人、千尋、蘇菲,都只是這些故事中的一個引信,他們駝著的不明課題其實都是自己的身份漩渦。
在故事中圍繞著他們的那些角色們,也總有自己的課題,宮崎駿從不賦予一個角色真正的英雄,而是讓這些人物的困難圍繞在一個共同的命題上打轉:你了解自己的身份嗎?你喜歡嗎?如果不喜歡,你能怎麼辦呢?
而在我看來,包含在這一次《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宮崎駿在一貫半開放又正面的故事收尾中,為這共同的課題打了一道光:
「無論如何,人是無法沒有身份的。活在世上,你總會被賦予或爭取到一個身份的。」
生於一個在現代化歷程中不斷追問自己是誰的國家,宮崎駿的作品有他生於戰爭時期,極富昭和風格的故事剪裁。在世界戰火之間,遇到這部傳聞中的封筆之作,坐在影廳內,看著Roll Card不斷往上跑動之際,我腦袋在想的是,既然,我們都無法擺脫毫無身份的人生,也總焦慮於身份是否足以襯托自己的心理框架;也許,宮崎駿更進一步面向我們拋出的課題是:「我可以怎麼看待自己是誰?」
平野啟一郎在《那個男人》(原文:ある男)中,透過不同身份的錯置、掩藏、遺失,交織出每個人的人生其實都會回到自我凝視的提問。一個掩藏自己是在日朝鮮人身份的律師、一個借用他人身份,尋找到人生幸福卻意外喪命的男子、一個失去丈夫後卻發現丈夫生前的身份其實是借用的妻子,平野啟一郎透過書中律師城戶自顧自地,問出:
「如此一來,當我們愛上一個人,究竟是愛那個人的什麼呢?⋯⋯先是對眼前的這個人抱持好感,然後,愛上這個人包含他的過去。可是,如果知道了這個人的過去是別人的,那麼兩人之間的愛會該何去何從?」
人生是受限的,受限於身份。但《那個男人》中交錯的角色無論身份的真偽,卻尖銳地凸顯出感情的真實。在情感流動與人生的前進步伐中,身份是一個載體,不是生活的根源。然而,存在的不安總會反映在身份政治的問題上。所以,我們看到小至文學中一個一個人因身份而有的脫序決定;宮崎駿畫筆中的一個一個冒險。然而,我們卻在真實人生中看到因身份背後的歷史與眼前的未來,導引出更巨大的衝突,如此刻的以巴問題。
因身份政治衝突下的戰火,將一個一個生命與人生捲入漩渦中。如果我們近身凝視那些生命的特寫,無論哪一方都不忍卒睹。然而,回到撐起身份的那些歷史與共同體感,屬於誰的義憤幾乎要攔腰折斷另一方的脊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