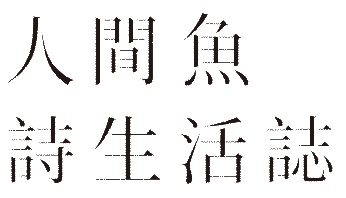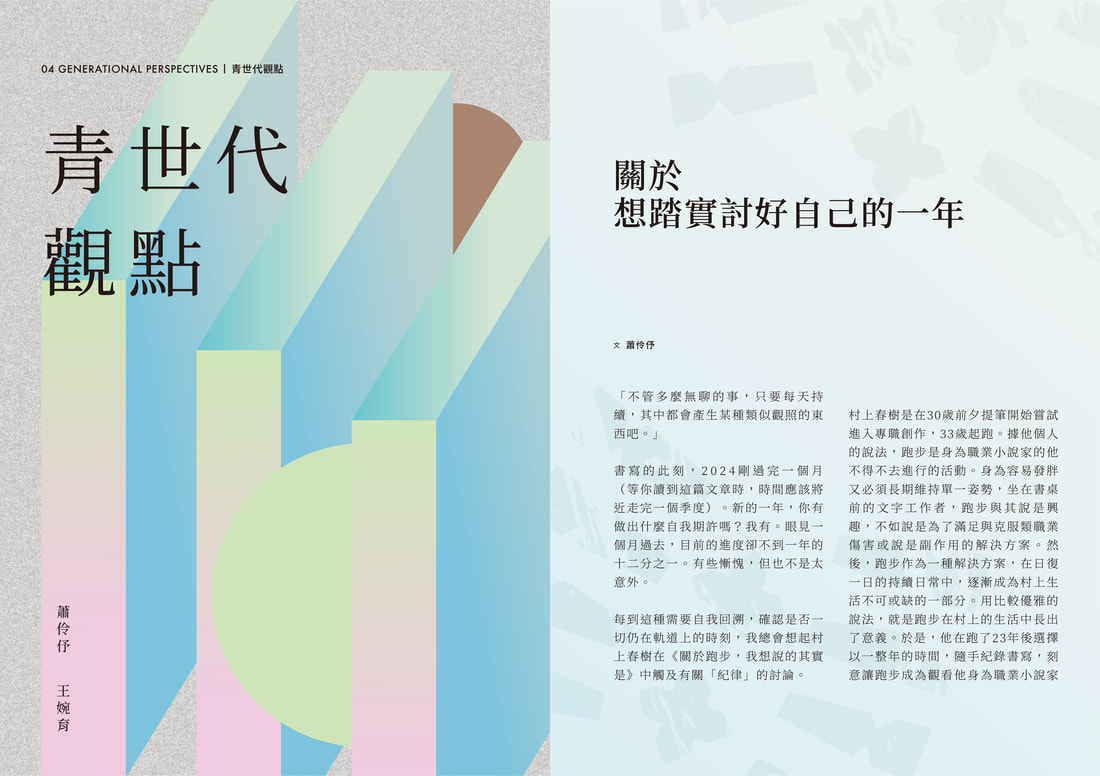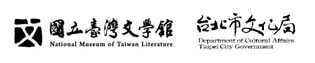關於想踏實討好自己的一年
青世代觀點|蕭伶伃專欄
文|蕭伶伃
「不管多麼無聊的事,只要每天持續,其中都會產生某種類似觀照的東西吧。」
書寫的此刻,2024剛過完一個月(等你讀到這篇文章時,時間應該將近走完一個季度)。新的一年,你有做出什麼自我期許嗎?我有。眼見一個月過去,目前的進度卻不到一年的十二分之一。有些慚愧,但也不是太意外。
每到這種需要自我回溯,確認是否一切仍在軌道上的時刻,我總會想起村上春樹在《關於跑步,我想說的其實是》中觸及有關「紀律」的討論。
村上春樹是在30歲前夕提筆開始嘗試進入專職創作,33歲起跑。據他個人的說法,跑步是身為職業小說家的他不得不去進行的活動。身為容易發胖又必須長期維持單一姿勢,坐在書桌前的文字工作者,跑步與其說是興趣,不如說是為了滿足與克服類職業傷害或說是副作用的解決方案。然後,跑步作為一種解決方案,在日復一日的持續日常中,逐漸成為村上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比較優雅的說法,就是跑步在村上的生活中長出了意義。於是,他在跑了23年後選擇以一整年的時間,隨手紀錄書寫,刻意讓跑步成為觀看他身為職業小說家或說是一個人的切角,反思跑步在他人生扮演的角色。
其實,我並不算是村上的書迷。縱使讀過且收藏他在繁體中文市場出版的大部分作品,但他並非我最喜愛的日本當代小說家。真正讓我對這個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作品,反而是較貼近以跑步延伸出的雜談《關於跑步,我想說的其實是》。第一次讀,我人正在博士班階段,也是鎮日在書案前的生活。那段在英國劍橋的小鎮日子,我人除了在圖書館、系館之外,就是在家裡的書桌;再不然,就是廚房。一天之中,坐著閱讀與寫字的時間既連續又破碎。生活彷彿被切割成寫字與沒有寫字的時刻。
我記得自己當時讀到村上這本書時,極為震撼。心想,「那我明明也有這樣的需求,如何讓需求延伸出紀律?所以,是不是該起跑了?」可惜,這個需求當時並未真正在我心底扎根。我終究是相當頑固地以賣弄青春的方式度日。偶爾打打壁球、有一搭沒一打的跑著,啤酒與GIN TONIC一整套,瑜伽做半套,就這樣度過了博士班生涯,筆耕數萬字,體脂也越來越高。
一直到這兩年,我才真正面對自己這份早該浮現的需求。前年秋天,我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家人。無法面對悲傷,只好選擇起跑。這前後字句毫無邏輯關聯,但在我心中確實是這麼展開的。我穿上了亞瑟士的紫色跑鞋,在只有200公尺的操場上,一圈又一圈地跑著。跟著線上的馬拉松課表,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拼命地跑,但當時的我,只能藉由跑步,讓自己放空。讓自己適應而不是忘記悲傷。悲傷無法被遺忘,至少,我得找到讓身體適應它的方式。我下雨天也跑,寒流來也跑,大太陽也跑。唯獨辦不到的事情就是清晨起床路跑。我是夜光跑者。跑著跑著,就像是這篇文章開頭置頂的那句話:「再怎麼無聊的事,只要每天持續,其中都會產生某種類似觀照的東西吧。」
有那麼一天,我記得是週五傍晚,在應酬前,我趕回家換上跑鞋,只為先跑個五公里再赴約。那天微微細雨,天氣微涼,我跑著跑著,突然感覺到另一個自己可以看到正在跑步的自己。我感覺到微風跑步的速度讓雨打在臉上的刺痛感,也感覺到風穿過我腰間的幅度;同時,我看見我自己 ——正在跑步的自己。
突然間,我意識到跑步這件事,已經不是為了適應悲傷,也不是為了賽事。它就是跑步,也只是跑步,但它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會長出與自己本質相近的樣子,甚至,我我感覺到,它不是紀律,更像是一種「討好」:只為自己的好好生活而發生的「討好」。當距離拉長,只要還在忍受範圍,它就像是村上說的:「脫離日常性,基本上沒有違反人道的行為。」
我把它解讀成,跑步有「我的跑步」、「村上的跑步」與「OOO的跑步」這麼多種。也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每個人跨進半馬或全馬的終點線的心情與姿態都不同。當跑步持續了一年多,我開始遇到因為職涯轉換,必須重新規劃讓跑步得以順利在生活存續下來的方案。有點像是一場戀愛關係中,如何不讓自己與對方的關係因為生活節奏的變動,而產生斷裂。但我是不會輕易說跑步於我像是戀愛,因為我不想談這麼無聊又辛苦的戀愛。
時至今日,我仍然無法說我熱愛跑步。但在不斷積累、長出屬於「我的跑步」的成就感與樂趣,確實仍在日復一日的無聊訓練中,盎然生長著。我仍不時為了不夠有「紀律」而暗自懊悔,但卻也在偷懶與勤奮間,持續讓跑步以更貼近自己本質的方式存在著。跑步也不再是我與誰的競爭,或是我與我自己的競爭。相反的,它更像是我與自己的對話。
身為長期在做研究與發想的策略工作者,在大腦中自言自語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跑步就像是一個次元空間,是我可以盡情把各種思緒與想法往裡面丟的世界。在那裡,有很多事不會立即有解答,但過一段時間,總會有新的反饋在呼吸與喘息間迸發出來。
也因此,當跑步成為一種職業,必須去爭個輸贏時,對我來說,已超出村上所描述的世界。就像是今年一月,大阪女子馬剛破日本女性全馬紀錄,跑出2小時18分59秒的前田穂南。她在東京奧運時,跑得並不理想。在其後赴美的訓練中,當隨行影像記錄問她,妳所設下的目標是什麼?
「那個。」(日文:あれ)前田不帶任何表情地答道。無論怎麼追問,前田僅是簡短重複著答案。最終,她在細雨中破了日本女性的全馬紀錄。邁向終點前的她,拿下墨鏡,看似仍有氣力,相對輕鬆地跑進日本的全新紀錄中。我深深為了她的答案而感覺到震撼。我不禁腦補想著,對前田這樣的世界級選手來說,跑步似乎仍然有她與自己對話的私密感,而不僅僅是個人的挑戰與職業而已。
或像是緊追在其後,最終仍抱憾闖過終點線的佐藤早也伽。她在去年大阪女子馬遭到其他選手意外撞倒跌傷後,被迫中途退賽。佐藤過去一整年花了相當大的氣力在準備,只為了爭取2024巴黎奧運的代表資格。今年再次站上同樣的賽道上,佐藤在踏入終點線時,卻已明顯露出疲態。衝過充點線後的她並未舉起勝利手勢,相反的,是不支倒地。賽後,佐藤談到自己仍然不足,但已盡了全力。
比起前田或佐藤這樣的世界級選手,我們的跑步,都仍保有進退的餘裕。甚至,都是幫助我們在人生軌道上的一項方案。然而,我真正想說的是,如果你的計畫,沒有要討好誰(儘管我們都認為討好別人很奇怪,但我們其實總是這麼生活著,不過這又是另一個題目了),請記得一定要討好自己。讓自己好好生活下去的那種討好。讓自己找到安靜自在生活的方式。當然,我不是想要鼓勵你去跑步。相信我,跑步真的很無聊。它如果有任何樂趣,都必須要在形成習慣之後,才有發生的可能。
而我只是想說,今年,你的計畫上了軌道了嗎?
你讓計畫慢慢融進你的生活了嗎?
如果還沒,去讀讀村上吧。
他也許會給你怎麼討好自己的答案。
書寫的此刻,2024剛過完一個月(等你讀到這篇文章時,時間應該將近走完一個季度)。新的一年,你有做出什麼自我期許嗎?我有。眼見一個月過去,目前的進度卻不到一年的十二分之一。有些慚愧,但也不是太意外。
每到這種需要自我回溯,確認是否一切仍在軌道上的時刻,我總會想起村上春樹在《關於跑步,我想說的其實是》中觸及有關「紀律」的討論。
村上春樹是在30歲前夕提筆開始嘗試進入專職創作,33歲起跑。據他個人的說法,跑步是身為職業小說家的他不得不去進行的活動。身為容易發胖又必須長期維持單一姿勢,坐在書桌前的文字工作者,跑步與其說是興趣,不如說是為了滿足與克服類職業傷害或說是副作用的解決方案。然後,跑步作為一種解決方案,在日復一日的持續日常中,逐漸成為村上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比較優雅的說法,就是跑步在村上的生活中長出了意義。於是,他在跑了23年後選擇以一整年的時間,隨手紀錄書寫,刻意讓跑步成為觀看他身為職業小說家或說是一個人的切角,反思跑步在他人生扮演的角色。
其實,我並不算是村上的書迷。縱使讀過且收藏他在繁體中文市場出版的大部分作品,但他並非我最喜愛的日本當代小說家。真正讓我對這個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作品,反而是較貼近以跑步延伸出的雜談《關於跑步,我想說的其實是》。第一次讀,我人正在博士班階段,也是鎮日在書案前的生活。那段在英國劍橋的小鎮日子,我人除了在圖書館、系館之外,就是在家裡的書桌;再不然,就是廚房。一天之中,坐著閱讀與寫字的時間既連續又破碎。生活彷彿被切割成寫字與沒有寫字的時刻。
我記得自己當時讀到村上這本書時,極為震撼。心想,「那我明明也有這樣的需求,如何讓需求延伸出紀律?所以,是不是該起跑了?」可惜,這個需求當時並未真正在我心底扎根。我終究是相當頑固地以賣弄青春的方式度日。偶爾打打壁球、有一搭沒一打的跑著,啤酒與GIN TONIC一整套,瑜伽做半套,就這樣度過了博士班生涯,筆耕數萬字,體脂也越來越高。
一直到這兩年,我才真正面對自己這份早該浮現的需求。前年秋天,我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家人。無法面對悲傷,只好選擇起跑。這前後字句毫無邏輯關聯,但在我心中確實是這麼展開的。我穿上了亞瑟士的紫色跑鞋,在只有200公尺的操場上,一圈又一圈地跑著。跟著線上的馬拉松課表,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拼命地跑,但當時的我,只能藉由跑步,讓自己放空。讓自己適應而不是忘記悲傷。悲傷無法被遺忘,至少,我得找到讓身體適應它的方式。我下雨天也跑,寒流來也跑,大太陽也跑。唯獨辦不到的事情就是清晨起床路跑。我是夜光跑者。跑著跑著,就像是這篇文章開頭置頂的那句話:「再怎麼無聊的事,只要每天持續,其中都會產生某種類似觀照的東西吧。」
有那麼一天,我記得是週五傍晚,在應酬前,我趕回家換上跑鞋,只為先跑個五公里再赴約。那天微微細雨,天氣微涼,我跑著跑著,突然感覺到另一個自己可以看到正在跑步的自己。我感覺到微風跑步的速度讓雨打在臉上的刺痛感,也感覺到風穿過我腰間的幅度;同時,我看見我自己 ——正在跑步的自己。
突然間,我意識到跑步這件事,已經不是為了適應悲傷,也不是為了賽事。它就是跑步,也只是跑步,但它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會長出與自己本質相近的樣子,甚至,我我感覺到,它不是紀律,更像是一種「討好」:只為自己的好好生活而發生的「討好」。當距離拉長,只要還在忍受範圍,它就像是村上說的:「脫離日常性,基本上沒有違反人道的行為。」
我把它解讀成,跑步有「我的跑步」、「村上的跑步」與「OOO的跑步」這麼多種。也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每個人跨進半馬或全馬的終點線的心情與姿態都不同。當跑步持續了一年多,我開始遇到因為職涯轉換,必須重新規劃讓跑步得以順利在生活存續下來的方案。有點像是一場戀愛關係中,如何不讓自己與對方的關係因為生活節奏的變動,而產生斷裂。但我是不會輕易說跑步於我像是戀愛,因為我不想談這麼無聊又辛苦的戀愛。
時至今日,我仍然無法說我熱愛跑步。但在不斷積累、長出屬於「我的跑步」的成就感與樂趣,確實仍在日復一日的無聊訓練中,盎然生長著。我仍不時為了不夠有「紀律」而暗自懊悔,但卻也在偷懶與勤奮間,持續讓跑步以更貼近自己本質的方式存在著。跑步也不再是我與誰的競爭,或是我與我自己的競爭。相反的,它更像是我與自己的對話。
身為長期在做研究與發想的策略工作者,在大腦中自言自語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跑步就像是一個次元空間,是我可以盡情把各種思緒與想法往裡面丟的世界。在那裡,有很多事不會立即有解答,但過一段時間,總會有新的反饋在呼吸與喘息間迸發出來。
也因此,當跑步成為一種職業,必須去爭個輸贏時,對我來說,已超出村上所描述的世界。就像是今年一月,大阪女子馬剛破日本女性全馬紀錄,跑出2小時18分59秒的前田穂南。她在東京奧運時,跑得並不理想。在其後赴美的訓練中,當隨行影像記錄問她,妳所設下的目標是什麼?
「那個。」(日文:あれ)前田不帶任何表情地答道。無論怎麼追問,前田僅是簡短重複著答案。最終,她在細雨中破了日本女性的全馬紀錄。邁向終點前的她,拿下墨鏡,看似仍有氣力,相對輕鬆地跑進日本的全新紀錄中。我深深為了她的答案而感覺到震撼。我不禁腦補想著,對前田這樣的世界級選手來說,跑步似乎仍然有她與自己對話的私密感,而不僅僅是個人的挑戰與職業而已。
或像是緊追在其後,最終仍抱憾闖過終點線的佐藤早也伽。她在去年大阪女子馬遭到其他選手意外撞倒跌傷後,被迫中途退賽。佐藤過去一整年花了相當大的氣力在準備,只為了爭取2024巴黎奧運的代表資格。今年再次站上同樣的賽道上,佐藤在踏入終點線時,卻已明顯露出疲態。衝過充點線後的她並未舉起勝利手勢,相反的,是不支倒地。賽後,佐藤談到自己仍然不足,但已盡了全力。
比起前田或佐藤這樣的世界級選手,我們的跑步,都仍保有進退的餘裕。甚至,都是幫助我們在人生軌道上的一項方案。然而,我真正想說的是,如果你的計畫,沒有要討好誰(儘管我們都認為討好別人很奇怪,但我們其實總是這麼生活著,不過這又是另一個題目了),請記得一定要討好自己。讓自己好好生活下去的那種討好。讓自己找到安靜自在生活的方式。當然,我不是想要鼓勵你去跑步。相信我,跑步真的很無聊。它如果有任何樂趣,都必須要在形成習慣之後,才有發生的可能。
而我只是想說,今年,你的計畫上了軌道了嗎?
你讓計畫慢慢融進你的生活了嗎?
如果還沒,去讀讀村上吧。
他也許會給你怎麼討好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