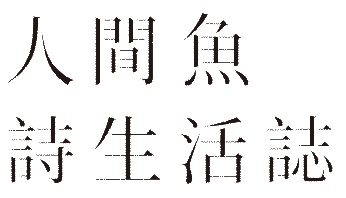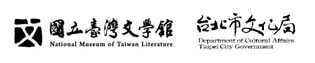面向尚未挖掘的部分:以詩探觸自身與族群
專訪 嚴毅昇(Cidal)
採訪撰文 | 郭瀅瀅
攝影 | 郭潔渝
攝影 | 郭潔渝
戴著墨綠色眼鏡的嚴毅昇,臉上有股斯文的少年氣息,目光卻暗藏著擱淺的憂傷。訪答裡的他縝密而嚴謹,文字閒聊中的他則是幽默活潑,像一個奔放的男孩。
封面拍攝當天一起午餐,才知道原來他吃素。我擔憂他只有玉米湯可以喝,所以把攜帶的白饅頭遞給他。而他吃得很習慣,我想他的食物必定都很清淡。除了詩以外的創作,毅昇也畫畫,在那些他向我分享的畫作裡,筆下的獸呈現了他內在爆發性的生猛能量,紙張隨著強勁細密的筆觸凹陷,紙背必定滿是凸起的痕跡。好像我年少時的髮,豎起,每根都帶著自身的傷口與血液。沒有問他作畫當下的內心狀態,也許正如訪談中他提及自己的詩,因著一種「相對剝奪感」而充滿衝撞性質。不迴避暗面,他會面向它們,而此刻他也步入另一個進程,當下的油墨已乾,每一道軌跡與線條仍在紙上發亮。
詩:另一個聲道、自我梳理的痕跡
郭:你是哪時候開始寫詩的?詩在你的生活裡,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嚴:就讀中文系大二時,接觸到系上教授的創作課程,才慢慢地開始認真閱讀現代詩,在此之前都是從課綱教條下的課本中認識詩,當時創作認知的門被打開,亦受到教授鼓勵投稿校內文學獎,摸索寫詩是什麼樣的行動與思考形式,詩在我的生活中基本上是一種食用精神糧食後所留下的成份記錄,精神糧食不見得是書籍,可以是音樂、電影,或者各種藝術、知識;一處氛圍特殊的所在;他人或自身的成長體悟與生活經歷。
當你去啃食其中集結的思維,詩會是一種呈現心靈富足或匱乏時的反彈力道,他像是身心靈進入某種狀態時汩汩流出的副產品。
如果要問詩具有什麼意義,我反而想要問自己「為什麼是(選擇)詩。」我會說,那是我另一個聲道,也是自我梳理的痕跡,像是我喜歡的詩人阿多尼斯的詩集名《時光的皺紋》。
郭:你的詩裡常有以抗爭運動為主的題材,像是收錄在《劃出回家的路──為傳統領域夜宿凱道day700+影‧詩》的《野放》,還有你尚未發表,以反送中行動為題材的《你此刻站立的位置》。而你也實際現身許多原運行動,請你談談詩在社會參與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你是否相信詩的社會功用?(又或者是這對你來說,純粹是一種很個人的、不得不的書寫與表達?)
嚴:對我來說詩有一定的傳播功能性,比小說、散文更快的表達意旨,這也是在台灣社會的文學史中有「反共戰鬥詩」的原因,我認為所謂「不得不」有兩種,一種是反擊,第二種是為了生存,相比許多青年運動者與原運世代的前輩我其實參與甚少,但作為「一種在第二線、第三線聲援的方法」,詩無疑地是最快速的、數量也是最多的,這在《衛生紙詩刊+》中與各大文學獎中亦能看見,社會對於不義議題的反彈力道,大至家國社會,近至我族與私生活,一如〈野放〉這首詩是為了支持在凱達格蘭大道與二二八公園中露宿抗議的巴奈、那布與馬耀的行動所寫詩之一,當時利格拉樂.阿烏老師廣邀族人與關注此議題的知名作家一同參與「凱道 船來 一首詩」為凱道上夜宿抗爭的族人們支持、打氣的活動。
我相信民主國家應賦予所有人進行社會運動的公民權力,無論大小,都是在推進社會的一小步。
〈你此刻站立的位置〉這首詩表達的是一種我非在場者,但深感政治威脅的情狀,並表達質疑自己是否有對香港政局現況發言的資格,以及對於抗爭場合的熟悉與疏離。詩或許能透過網路傳送代替我們抵達任何遙遠的受難地。
一如政治並不純粹,人類是很渾沌的存在,如欲投身運動之中必然要有其認知,「這絕非是個人的」,即使你正在進行一個人的運動,你還是在群體的利益中鬥爭。某方面來說我不認為自己是具有正義感的人,而是在生活許可的時候,做應該做的事,「這世界不是只有自己存在,不要過分的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學習的事。
封面拍攝當天一起午餐,才知道原來他吃素。我擔憂他只有玉米湯可以喝,所以把攜帶的白饅頭遞給他。而他吃得很習慣,我想他的食物必定都很清淡。除了詩以外的創作,毅昇也畫畫,在那些他向我分享的畫作裡,筆下的獸呈現了他內在爆發性的生猛能量,紙張隨著強勁細密的筆觸凹陷,紙背必定滿是凸起的痕跡。好像我年少時的髮,豎起,每根都帶著自身的傷口與血液。沒有問他作畫當下的內心狀態,也許正如訪談中他提及自己的詩,因著一種「相對剝奪感」而充滿衝撞性質。不迴避暗面,他會面向它們,而此刻他也步入另一個進程,當下的油墨已乾,每一道軌跡與線條仍在紙上發亮。
詩:另一個聲道、自我梳理的痕跡
郭:你是哪時候開始寫詩的?詩在你的生活裡,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嚴:就讀中文系大二時,接觸到系上教授的創作課程,才慢慢地開始認真閱讀現代詩,在此之前都是從課綱教條下的課本中認識詩,當時創作認知的門被打開,亦受到教授鼓勵投稿校內文學獎,摸索寫詩是什麼樣的行動與思考形式,詩在我的生活中基本上是一種食用精神糧食後所留下的成份記錄,精神糧食不見得是書籍,可以是音樂、電影,或者各種藝術、知識;一處氛圍特殊的所在;他人或自身的成長體悟與生活經歷。
當你去啃食其中集結的思維,詩會是一種呈現心靈富足或匱乏時的反彈力道,他像是身心靈進入某種狀態時汩汩流出的副產品。
如果要問詩具有什麼意義,我反而想要問自己「為什麼是(選擇)詩。」我會說,那是我另一個聲道,也是自我梳理的痕跡,像是我喜歡的詩人阿多尼斯的詩集名《時光的皺紋》。
郭:你的詩裡常有以抗爭運動為主的題材,像是收錄在《劃出回家的路──為傳統領域夜宿凱道day700+影‧詩》的《野放》,還有你尚未發表,以反送中行動為題材的《你此刻站立的位置》。而你也實際現身許多原運行動,請你談談詩在社會參與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你是否相信詩的社會功用?(又或者是這對你來說,純粹是一種很個人的、不得不的書寫與表達?)
嚴:對我來說詩有一定的傳播功能性,比小說、散文更快的表達意旨,這也是在台灣社會的文學史中有「反共戰鬥詩」的原因,我認為所謂「不得不」有兩種,一種是反擊,第二種是為了生存,相比許多青年運動者與原運世代的前輩我其實參與甚少,但作為「一種在第二線、第三線聲援的方法」,詩無疑地是最快速的、數量也是最多的,這在《衛生紙詩刊+》中與各大文學獎中亦能看見,社會對於不義議題的反彈力道,大至家國社會,近至我族與私生活,一如〈野放〉這首詩是為了支持在凱達格蘭大道與二二八公園中露宿抗議的巴奈、那布與馬耀的行動所寫詩之一,當時利格拉樂.阿烏老師廣邀族人與關注此議題的知名作家一同參與「凱道 船來 一首詩」為凱道上夜宿抗爭的族人們支持、打氣的活動。
我相信民主國家應賦予所有人進行社會運動的公民權力,無論大小,都是在推進社會的一小步。
〈你此刻站立的位置〉這首詩表達的是一種我非在場者,但深感政治威脅的情狀,並表達質疑自己是否有對香港政局現況發言的資格,以及對於抗爭場合的熟悉與疏離。詩或許能透過網路傳送代替我們抵達任何遙遠的受難地。
一如政治並不純粹,人類是很渾沌的存在,如欲投身運動之中必然要有其認知,「這絕非是個人的」,即使你正在進行一個人的運動,你還是在群體的利益中鬥爭。某方面來說我不認為自己是具有正義感的人,而是在生活許可的時候,做應該做的事,「這世界不是只有自己存在,不要過分的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學習的事。
切身經歷的衝擊思索,是寫詩的驅動
郭:據我所知,你的母親為阿美族,父親為漢人,而你是在「原住民藝能班」裡才得到關於原住民文化的啟蒙?能否談談這部分,以及這對你在創作上的影響。
嚴:關於原住民文化的啟蒙,其實最早並不來自於原住民藝能班,而是某一年我們家曾到別的阿美族村落旁觀祭典樂舞,印象模糊當時應該還沒上小學(幾歲已不可考),在很小的時候就思考著那種既熟悉又疏離的感覺到底該怎麼稱呼,高中時我主動報考原住民專班,才發覺,那是一種在都市生活的原住民,或是體認了部落受宗教殖民而無法祭祖與舉辦祭儀的「尷尬感」。到近年又理解到外公、外婆的信仰使她們不能唱詩歌以外的族語歌曲,有一種「只剩下語言」的民族無奈,我對這些思考生活後所受衝擊的經驗的理解──那是一種「驅動」,使我去寫,因為那與我有關係。
董恕明教授曾稱這種人為「一胞半」,我的母親因襲外公而具有阿美血統,我的父親是生於恆春的漢人,我的外婆是噶瑪蘭族人,混雜紛呈於我的軀體內而矛盾。北上就讀幼稚園前我住在恆春的公嬤家,語言環境趨於台語,在幼稚園開始學習注音,族語遠遠排在後頭,於我而言更難學習的精神文化。
高中畢業以後,我的族服老師犁百·辛系曾私訊我,希望我多寫一些跟阿美族文化有關的文字,無論是詩、散文什麼都好,讓我覺得自己是有被看見的,但也是一種壓力。對於文化有一定的認識以後,我也特別小心語言使用的對錯問題,在進行有關原住民文學的寫作時,我總會想著如何釋放更多訊息,正在努力尋找一種妥適的平衡。
郭:你是如何看待「都市原住民」這個定義?你會介意這樣的標籤嗎?
嚴:這個稱呼我曾經使用過,基本上不會排斥,但那確實是一種「權宜」的稱呼。
我曾和Temu(黃璽)曾討論過「都市原住民」這個說法,他說:「這是一種『過渡』的狀態,如果你作為一位想返回部落的族人,你就不要以此為自居。」我十分認同這樣的觀點,如果未來我住在部落,我的狀態就不會是「都市」原住民,又另一點來說,「原住民」這三個字本身本就是政治詞彙,它代表一種主權與自我認同,不會因為居住何處而改變他的原來意義。
如果我在返鄉的過程中,被「標籤」為都市原住民,我固然是會介意,但在都市中被稱為都市原住民,卻又沒有那麼衝突,我認為這是隨著所處位置、對象而游移的,如果要這麼定義年輕一代較少機會接觸自族文化的青年,「現代原住民」或許是較為精確的稱呼法。
「想像部落」的迷思、文學的刻板
郭:你的詩作《不在之地》獲第12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佳作,也就是今年的事情,你近日也才剛領獎,這個獎項對你的意義是什麼?也請你談談這首詩的創作情境。
嚴:知曉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應該有六年了吧,這是第二次領獎,頒獎當天看到金山高中藝能班的表演,想起高中跳樂舞,參訪金山高中原住民專班的記憶,內心有些觸動。
這個獎項是有歷史象徵性的,是對於台灣原住民籍的創作者的肯定,但我不免去思考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的籌畫與評審組成是否年年更好?我會有更多的期許在於不同世代之間對於原住民籍創作者的未來有更多討論,其實所有的文學獎都是一瞬間幸運與榮耀的展示,真正的是得獎之後,我們會不會有更多省思,在評審的言談中獲得學習,或者是反駁與批判,更甚者是捍衛一種主體性,不要在獎座前迷失與流連太多,如果我們還要走創作這條路,文學獎是一種輔助與支持,一點點對於創作者的貼補,要嚴肅的思考它的功能與未來延續性。
正如過去我曾批判過原住民族文學獎過於追求「想像部落」的一種迷思,或者「原民性」,無意識或有意識地戴上一種觀看原住民族文學創作的濾鏡,形成一種文學的刻板,或是得獎體。「什麼是文字能帶我們去更遠的地方,反過來說,我們又帶文字去了多遠?」我不斷思忖著我與原住民族文學的距離有多遠。
〈不在之地〉是我近幾年返鄉的經驗汲取出的一滴反饋。
試論我母親的故鄉──長濱Sadida’an遭遇的宗教殖民與鄉村政治現代化過程,各種勢力交錯之下的生活景況,我不斷思考所發現的尷尬,它們像不義遺址一樣建立在實景之上,在村人進入部落時會有一座拱門上寫著「上田組部落」,那曾是讓我疑惑的五個字,在認識自族文化時,我必然也明白了長濱海階上的下田組、田組、上田組,這一層層遞近向山的日治時期規劃的行政區,尚未回復傳統的名字,當地有滿滿的水田與黑土,但你少見小米,也沒有人會在工作時一邊唱著〈鋤草歌〉,西部來的我思考著,那些已消失的是否還能視為當地人的文化傳統?
或許鄒族菁英高一生那句:「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水田不要賣。」其實也訴說著其他不應該被換掉、賣掉的傳統文化。
郭:據我所知,你的母親為阿美族,父親為漢人,而你是在「原住民藝能班」裡才得到關於原住民文化的啟蒙?能否談談這部分,以及這對你在創作上的影響。
嚴:關於原住民文化的啟蒙,其實最早並不來自於原住民藝能班,而是某一年我們家曾到別的阿美族村落旁觀祭典樂舞,印象模糊當時應該還沒上小學(幾歲已不可考),在很小的時候就思考著那種既熟悉又疏離的感覺到底該怎麼稱呼,高中時我主動報考原住民專班,才發覺,那是一種在都市生活的原住民,或是體認了部落受宗教殖民而無法祭祖與舉辦祭儀的「尷尬感」。到近年又理解到外公、外婆的信仰使她們不能唱詩歌以外的族語歌曲,有一種「只剩下語言」的民族無奈,我對這些思考生活後所受衝擊的經驗的理解──那是一種「驅動」,使我去寫,因為那與我有關係。
董恕明教授曾稱這種人為「一胞半」,我的母親因襲外公而具有阿美血統,我的父親是生於恆春的漢人,我的外婆是噶瑪蘭族人,混雜紛呈於我的軀體內而矛盾。北上就讀幼稚園前我住在恆春的公嬤家,語言環境趨於台語,在幼稚園開始學習注音,族語遠遠排在後頭,於我而言更難學習的精神文化。
高中畢業以後,我的族服老師犁百·辛系曾私訊我,希望我多寫一些跟阿美族文化有關的文字,無論是詩、散文什麼都好,讓我覺得自己是有被看見的,但也是一種壓力。對於文化有一定的認識以後,我也特別小心語言使用的對錯問題,在進行有關原住民文學的寫作時,我總會想著如何釋放更多訊息,正在努力尋找一種妥適的平衡。
郭:你是如何看待「都市原住民」這個定義?你會介意這樣的標籤嗎?
嚴:這個稱呼我曾經使用過,基本上不會排斥,但那確實是一種「權宜」的稱呼。
我曾和Temu(黃璽)曾討論過「都市原住民」這個說法,他說:「這是一種『過渡』的狀態,如果你作為一位想返回部落的族人,你就不要以此為自居。」我十分認同這樣的觀點,如果未來我住在部落,我的狀態就不會是「都市」原住民,又另一點來說,「原住民」這三個字本身本就是政治詞彙,它代表一種主權與自我認同,不會因為居住何處而改變他的原來意義。
如果我在返鄉的過程中,被「標籤」為都市原住民,我固然是會介意,但在都市中被稱為都市原住民,卻又沒有那麼衝突,我認為這是隨著所處位置、對象而游移的,如果要這麼定義年輕一代較少機會接觸自族文化的青年,「現代原住民」或許是較為精確的稱呼法。
「想像部落」的迷思、文學的刻板
郭:你的詩作《不在之地》獲第12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佳作,也就是今年的事情,你近日也才剛領獎,這個獎項對你的意義是什麼?也請你談談這首詩的創作情境。
嚴:知曉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應該有六年了吧,這是第二次領獎,頒獎當天看到金山高中藝能班的表演,想起高中跳樂舞,參訪金山高中原住民專班的記憶,內心有些觸動。
這個獎項是有歷史象徵性的,是對於台灣原住民籍的創作者的肯定,但我不免去思考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的籌畫與評審組成是否年年更好?我會有更多的期許在於不同世代之間對於原住民籍創作者的未來有更多討論,其實所有的文學獎都是一瞬間幸運與榮耀的展示,真正的是得獎之後,我們會不會有更多省思,在評審的言談中獲得學習,或者是反駁與批判,更甚者是捍衛一種主體性,不要在獎座前迷失與流連太多,如果我們還要走創作這條路,文學獎是一種輔助與支持,一點點對於創作者的貼補,要嚴肅的思考它的功能與未來延續性。
正如過去我曾批判過原住民族文學獎過於追求「想像部落」的一種迷思,或者「原民性」,無意識或有意識地戴上一種觀看原住民族文學創作的濾鏡,形成一種文學的刻板,或是得獎體。「什麼是文字能帶我們去更遠的地方,反過來說,我們又帶文字去了多遠?」我不斷思忖著我與原住民族文學的距離有多遠。
〈不在之地〉是我近幾年返鄉的經驗汲取出的一滴反饋。
試論我母親的故鄉──長濱Sadida’an遭遇的宗教殖民與鄉村政治現代化過程,各種勢力交錯之下的生活景況,我不斷思考所發現的尷尬,它們像不義遺址一樣建立在實景之上,在村人進入部落時會有一座拱門上寫著「上田組部落」,那曾是讓我疑惑的五個字,在認識自族文化時,我必然也明白了長濱海階上的下田組、田組、上田組,這一層層遞近向山的日治時期規劃的行政區,尚未回復傳統的名字,當地有滿滿的水田與黑土,但你少見小米,也沒有人會在工作時一邊唱著〈鋤草歌〉,西部來的我思考著,那些已消失的是否還能視為當地人的文化傳統?
或許鄒族菁英高一生那句:「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水田不要賣。」其實也訴說著其他不應該被換掉、賣掉的傳統文化。
創作:以累積和觀察推敲琢磨,當下認為美好的樣子
郭:你每天都會寫詩嗎?關於一首詩的完成,你的創作經驗是怎麼樣的?
嚴:我剛開始學創作時幾乎每天都寫,但都不成形,依靠一種衝動,或者能解釋成新鮮感,我沒有所謂「老師」的概念,或者沒有固定的學習者,我喜歡一直變動,這和我閱讀、觀察的雜食性也有關聯,所以最早開始創作時會缺乏統一性、主題性,這也是說文學對我而言並沒有非寫不可的原因,卻是我最習以為常的表達自我的方式,或者一切都是過程,我正無意識前往一個「有目標的我」的路上也不一定。正如我很喜歡的一句話:「先成為人,才成為詩人。」學習與吸收並沒有所謂盡頭,只看我的創作能內化多少程度,能有多麼「混沌」。
後來接觸許多詩刊、網路詩社、校園詩社,我的核心想法沒有改變多少,但創作經驗與發表、評論經驗變得較多以後,我嘗試收束自己,不要釋放太多訊息、鋒芒,畢竟我還沒有出版經驗,近期正緩慢修整自己的創作與心理狀態,準備面對世界的指教。
近年的狀態因為生活與工作繁忙,寫下的都是隻字片語或短文,那些還未轉化成詩句的碎片,在某個時點,會突然被串聯起來成詩篇,很多時候我不是依靠靈感在創作,多是依靠累積和觀察去推敲琢磨,當下認為美好的樣子。
郭:你是否有在寫作上心裡特別崇敬的對象?他對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嚴:初接觸現代詩時,我很喜歡讀印度詩哲泰戈爾的詩,那種具哲理性,箴言式的懺語對生活很有啟示……
郭:你每天都會寫詩嗎?關於一首詩的完成,你的創作經驗是怎麼樣的?
嚴:我剛開始學創作時幾乎每天都寫,但都不成形,依靠一種衝動,或者能解釋成新鮮感,我沒有所謂「老師」的概念,或者沒有固定的學習者,我喜歡一直變動,這和我閱讀、觀察的雜食性也有關聯,所以最早開始創作時會缺乏統一性、主題性,這也是說文學對我而言並沒有非寫不可的原因,卻是我最習以為常的表達自我的方式,或者一切都是過程,我正無意識前往一個「有目標的我」的路上也不一定。正如我很喜歡的一句話:「先成為人,才成為詩人。」學習與吸收並沒有所謂盡頭,只看我的創作能內化多少程度,能有多麼「混沌」。
後來接觸許多詩刊、網路詩社、校園詩社,我的核心想法沒有改變多少,但創作經驗與發表、評論經驗變得較多以後,我嘗試收束自己,不要釋放太多訊息、鋒芒,畢竟我還沒有出版經驗,近期正緩慢修整自己的創作與心理狀態,準備面對世界的指教。
近年的狀態因為生活與工作繁忙,寫下的都是隻字片語或短文,那些還未轉化成詩句的碎片,在某個時點,會突然被串聯起來成詩篇,很多時候我不是依靠靈感在創作,多是依靠累積和觀察去推敲琢磨,當下認為美好的樣子。
郭:你是否有在寫作上心裡特別崇敬的對象?他對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嚴:初接觸現代詩時,我很喜歡讀印度詩哲泰戈爾的詩,那種具哲理性,箴言式的懺語對生活很有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