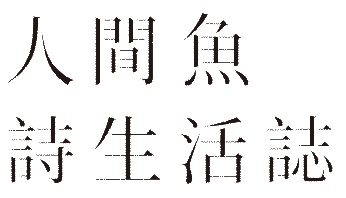選擇了文學的裸命:
以文字領航的夏曼‧藍波安
採訪撰文 | 蔡佩含
回顧1992年起始的《八代灣的神話》、以達悟男孩們的夢想和命運投射自我出走/歸返路徑的《黑色的翅膀》、紀錄了耆老們充滿皺摺與智慧臉孔的《海浪的記憶》、潛入海平面底下三十公尺的文學史經典之作《冷海情深》、回應現代性與傳統生態智慧的散文集《航海家的臉》;充滿辯證與批判的小說《天空的眼睛》、《老海人》、《安洛米恩之死》,尖銳挑起讀者直視小島命運,重新反思正常/異常、文明/野蠻的邊界;《大海浮夢》則引領讀者航向世界,建立從海洋觀點出發的世界連結;《大海之眼》與《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是最真誠赤裸的自述和告白;甫出版的新作《沒有信箱的男人》則以父祖輩們的記憶和口述,顛覆殖民者觀點的文字歷史,更帶出對無文字族群「被殖民歷史」的批判,亦是對全球原住民族命運的深沉詰問。
細數這一部部作品踏印出的文學軌跡,說明這三十多年來,「夏曼・藍波安」已經不只是當初洄游原鄉,掙扎於現實和文化傳承之間,努力在海潮浪濤裡證明自己的男人,而是透過一本又一本的作品堆疊,開創出不同向度的批判和思考,也已然建立了無法被取代的文學價值,並啟發了無數對族群文化、對海洋一無所知的我們。
但為何文學?為何書寫?當年加入街頭的行列衝撞體制,又策劃發起「驅除惡靈」蘭嶼反核行動的身影,在以身體復返文化空間後,為何選擇了文學?又究竟是什麼強大的動能,驅策著這耗費精氣神的文學志業持續至今?
在《大海浮夢》裡,夏曼曾敘述自己透過身體的展演與實踐,結合在地知識和現代性知識的書寫,並不是孩提時的夢想,也未曾想過成為一名海洋文學家。「成為作家」或許可以算是一種順其自然的導向,但也是一個不斷嘗試和碰撞的過程,在不同的經驗中慢慢找到自己的航線。夏曼憶及1985年7月,和胡德夫、丹耐夫正若等一行人,為了阿美族漁工在印尼被扣留的事件,前往行政院門口抗議,在那個當下,發覺自己雖會去抵抗殖民政權,也願意站出來為族群的權益奮鬥,但相比之下卻未具備革命鼓吹者那樣的人格特質,自己的個性比較沉默,也還是比較喜歡獨處和思考。
「我當時的問題是,我出了幾本書,但我還不知道有什麼意義,什麼叫做作家?我當時一直找我的身份,原來我是一個作家,這是我要找的身份。什麼理事長啊,什麼族群委員啊,那不是我要找的職業。所以你問我社會運動,是一個豐富化自己個人成長的過程,一個年齡階層在過程中的成長和歷練, 我是民族覺醒運動創造者,但絕不是藉著民族運動變成政客,因為我是不受主流社會馴化的人,因為我不是屬於那種安逸於現狀的人,而我的文學是我喜歡的工作, 我喜歡創作。」
從台北回到蘭嶼後,夏曼為了籌措蓋房子的資金,曾當了三年的學校教師,但卻覺得潛水射魚還比較不浪費生命,體感強烈的抗拒任何體制的框架和收編,回到海裡,才能找到一個人的寧靜。海人面對海洋總是保持謙遜的姿態,順從海洋的脾氣而「隨波逐流」;但是,作為一個海人,在漢人主導的體制下,卻已注定了無法順應主流的逆勢和孤獨。夏曼坦言,這個選擇了文學的裸命,「真的苦了太太和三個孩子」。但不願妥協,寧願成為「逆勢」作家的叛逆,也是「夏曼・藍波安」在文壇無可取代的理由。
以書寫抵抗殖民者的「發現主義」
「華人在學校的教育體制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改變的叫做『分數主義』。之前我到馬來西亞的獨立中學演講,我那時候說,不要去尊敬考那個第一名的,你們這些考第一名的,未來都是醫生,可是醫生都在看人體的疾病,卻看不到世界的疾病。我當時恭喜那些考58分、59分的,請他們全部都站起來,我說你們是我尊重的學生。學校的成績最終不是一個決定論,一個人的人生經歷,是自己要找出來的,不是人家跟你說你要走這條路,不是。」這種對學生的「勉勵」,相當獨樹一格,但也呼應了夏曼自己童年在「學校體制」的痛苦經驗,以及迄今的人生閱歷。
但這段談話,或許也是「為何文學」的答案之一,作為一個「逆勢」的文學家,更多時候是那個能夠看到「世界的疾病」,拆穿表面粉飾,並在逆流當中激盪出新的思辯,創造出獨到論述的思想領航者。而那也正是一部文學作品,能夠為世界帶來的豐富意義並且促成改變的巨大動能。
細數這一部部作品踏印出的文學軌跡,說明這三十多年來,「夏曼・藍波安」已經不只是當初洄游原鄉,掙扎於現實和文化傳承之間,努力在海潮浪濤裡證明自己的男人,而是透過一本又一本的作品堆疊,開創出不同向度的批判和思考,也已然建立了無法被取代的文學價值,並啟發了無數對族群文化、對海洋一無所知的我們。
但為何文學?為何書寫?當年加入街頭的行列衝撞體制,又策劃發起「驅除惡靈」蘭嶼反核行動的身影,在以身體復返文化空間後,為何選擇了文學?又究竟是什麼強大的動能,驅策著這耗費精氣神的文學志業持續至今?
在《大海浮夢》裡,夏曼曾敘述自己透過身體的展演與實踐,結合在地知識和現代性知識的書寫,並不是孩提時的夢想,也未曾想過成為一名海洋文學家。「成為作家」或許可以算是一種順其自然的導向,但也是一個不斷嘗試和碰撞的過程,在不同的經驗中慢慢找到自己的航線。夏曼憶及1985年7月,和胡德夫、丹耐夫正若等一行人,為了阿美族漁工在印尼被扣留的事件,前往行政院門口抗議,在那個當下,發覺自己雖會去抵抗殖民政權,也願意站出來為族群的權益奮鬥,但相比之下卻未具備革命鼓吹者那樣的人格特質,自己的個性比較沉默,也還是比較喜歡獨處和思考。
「我當時的問題是,我出了幾本書,但我還不知道有什麼意義,什麼叫做作家?我當時一直找我的身份,原來我是一個作家,這是我要找的身份。什麼理事長啊,什麼族群委員啊,那不是我要找的職業。所以你問我社會運動,是一個豐富化自己個人成長的過程,一個年齡階層在過程中的成長和歷練, 我是民族覺醒運動創造者,但絕不是藉著民族運動變成政客,因為我是不受主流社會馴化的人,因為我不是屬於那種安逸於現狀的人,而我的文學是我喜歡的工作, 我喜歡創作。」
從台北回到蘭嶼後,夏曼為了籌措蓋房子的資金,曾當了三年的學校教師,但卻覺得潛水射魚還比較不浪費生命,體感強烈的抗拒任何體制的框架和收編,回到海裡,才能找到一個人的寧靜。海人面對海洋總是保持謙遜的姿態,順從海洋的脾氣而「隨波逐流」;但是,作為一個海人,在漢人主導的體制下,卻已注定了無法順應主流的逆勢和孤獨。夏曼坦言,這個選擇了文學的裸命,「真的苦了太太和三個孩子」。但不願妥協,寧願成為「逆勢」作家的叛逆,也是「夏曼・藍波安」在文壇無可取代的理由。
以書寫抵抗殖民者的「發現主義」
「華人在學校的教育體制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改變的叫做『分數主義』。之前我到馬來西亞的獨立中學演講,我那時候說,不要去尊敬考那個第一名的,你們這些考第一名的,未來都是醫生,可是醫生都在看人體的疾病,卻看不到世界的疾病。我當時恭喜那些考58分、59分的,請他們全部都站起來,我說你們是我尊重的學生。學校的成績最終不是一個決定論,一個人的人生經歷,是自己要找出來的,不是人家跟你說你要走這條路,不是。」這種對學生的「勉勵」,相當獨樹一格,但也呼應了夏曼自己童年在「學校體制」的痛苦經驗,以及迄今的人生閱歷。
但這段談話,或許也是「為何文學」的答案之一,作為一個「逆勢」的文學家,更多時候是那個能夠看到「世界的疾病」,拆穿表面粉飾,並在逆流當中激盪出新的思辯,創造出獨到論述的思想領航者。而那也正是一部文學作品,能夠為世界帶來的豐富意義並且促成改變的巨大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