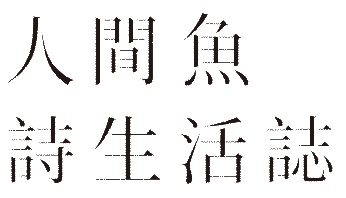斯卡羅之後——在天堂的邊緣,找回純粹的電影夢
專訪 曹瑞原
採訪 | 侯宗華
撰文 | 侯宗華
攝影 | 郭潔渝
撰文 | 侯宗華
攝影 | 郭潔渝
|
我首次觀看導演曹瑞原的作品,是刻劃台灣同志族群不為人知的壓抑、辛酸與悲劇的《孽子》。當時的我或許太年輕,只單純覺得故事很沉重悲傷,這樣大膽的題材讓我震撼不已。之後,在陸續堆出的《孤戀花》與《一把青》裡,我逐漸意識到曹導在影像裡呈現的眼淚與悲傷,蘊藏著極強烈的,對大時代裡小人物命運流轉的悲憫與照拂。2021年《斯卡羅》播出後,我感受到他的創作經歷了徹底的飛躍與蛻變,大量的中遠景構圖,讓觀影的體驗成了近乎客觀的上帝視角,劇中處處散發著一種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神秘與蒼涼。此時,我已經在瞬息萬變的影視行業裡打滾數年,正在籌拍我的第一部電影。
就在我的電影長片剛剛初剪完成,繁重的工作量幾乎耗竭了我所有的氣力與精神時,我終於有機會向曹導請益,便順勢將創作時經歷的所有困境、矛盾與疑惑,全都化成了訪題。 見面之前,我想像曹瑞原本人應該是一個目光如炬,骨相精實,不苟言笑,無時無刻散發出凜然威嚴的男子。採訪當天,我才發現他的身段纖瘦,渾身散發著寧靜的氣場,語氣謙和,卻又有著毫不保留的坦率與真誠。 曹導一坐下來就說,影視行業是需要熱情的,都是為了一點點的理想,工作之辛苦只比在地下挖礦的礦工稍微好一點啊!接著,他開始娓娓道來,在影視創作的道路上,那些飽含著悲與喜、掙扎與超越的生命歷程。講到拍片趣事時,他顯得眉飛色舞,笑得燦爛開懷,有時則低頭沉吟,彷彿正沉浸在拍片時,不斷逡巡流轉的聲音與光影之流當中。接著,又話鋒一轉,談起了拍攝《孽子》時,最讓他難以忘懷的回憶。 |
翻轉人生的電影與文學
「拍《孽子》的時候,阿青的媽媽流浪到歌舞團,後來生病的劇情,要找一個很簡陋的地方。我們在101前面找到了,那地方看上去是很不錯的大樓,可是走進地下室⋯⋯哇!樓上的汙水一直洩下來,裡頭住了一些遊民和老人,他們就在那邊擦澡。我們拍攝的時候,隔天還有孤獨死的老人被抬走,好慘啊!」曹瑞原搖頭苦笑著。
那一瞬間,我觀察到他全然地活在自己講述的故事裡,不僅對當時的拍攝細節,做了極為細膩的描繪與刻畫,也對周邊生活裡匍匐掙扎的底層人物,充滿真摯地同情與關懷。接著他談到了生命裡,造就他走向導演之路的起點,與命運般的轉折。
「我記得《魂斷藍橋》是國中時去看的。以那樣的年齡,會去看文藝片很奇怪,應該看個恐龍《哥吉拉》那種,結果我竟然去看《魂斷藍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男女主角的外型都是完美無瑕的,那種美與優雅非常吸引我。」曹導提起了年少時期在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電影時,雙眼靈活地轉動著,如同少年般,煥發出熱切純真的光芒。
「除了《魂斷藍橋》,我覺得生命中有很多安排,都一點一滴地讓你走向某個方向。其實,我畢業時是想要做攝影的,但那時『太陽系』MTV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店裡有很多影碟可以看外國電影,我就看到了一部電影。」曹導說。
「《魂斷威尼斯》?」我斗膽揣測。
「對!就是《魂斷威尼斯》。那部電影打開了我的新世界,我還記得故事是講述一個老人對一個青春男子的眷戀與遺憾。那部電影讓我開始覺得,攝影只是一個媒介,導演好像真正可以講故事。」曹導回憶著邁向導演之路的初心,感性地說。
接著,曹導述說起就讀世新大學的往事。當時,好友因找不到他而在桌上留下一本白先勇的《台北人》,從此翻轉了他的人生,讓他從一個不愛讀書、四肢發達的運動男孩蛻變成了纖細敏感的藝文青年。幾年的時光荏苒流逝了,畢業後的曹導進入影視行業後,某次在因緣際會下獲得了與公視合拍電視劇的機會,便主動提出希望將白先勇的《孽子》改編成電視劇,卻因為同志題材在當時較為敏感而遭到拒絕。想不到,一個禮拜之後,曹導在餐廳巧遇了白先勇,便主動向他表明了有意拍攝《孽子》的想法。當時,白先勇與曹導約定三天後再碰頭。那段期間,曹導向公視高層提出了《孽子》值得一拍的理由,與此同時,白先勇也因看了女同志題材人生劇展《童女之舞》,認為他能夠處理《孽子》的細膩情感,因而點頭答應。
聽見曹導的這番話,感覺彷彿有無形的命運之手,將《孽子》交付給了他,而他也不負眾望,將《孽子》轉化成同志影視題材的經典之作。2003年,台灣舉辦了華語圈首屆的同志遊行,當年《孽子》的播出,也在台灣引起了極為強烈的轟動與反響。我深信《孽子》以影像的力量,推波助瀾地促進了台灣同志平權的發展,曹導的選材目光,精準得不可思議!想到這裡,我試圖更深入地探索,曹導創作的養成,動機與脈絡。
「拍《孽子》的時候,阿青的媽媽流浪到歌舞團,後來生病的劇情,要找一個很簡陋的地方。我們在101前面找到了,那地方看上去是很不錯的大樓,可是走進地下室⋯⋯哇!樓上的汙水一直洩下來,裡頭住了一些遊民和老人,他們就在那邊擦澡。我們拍攝的時候,隔天還有孤獨死的老人被抬走,好慘啊!」曹瑞原搖頭苦笑著。
那一瞬間,我觀察到他全然地活在自己講述的故事裡,不僅對當時的拍攝細節,做了極為細膩的描繪與刻畫,也對周邊生活裡匍匐掙扎的底層人物,充滿真摯地同情與關懷。接著他談到了生命裡,造就他走向導演之路的起點,與命運般的轉折。
「我記得《魂斷藍橋》是國中時去看的。以那樣的年齡,會去看文藝片很奇怪,應該看個恐龍《哥吉拉》那種,結果我竟然去看《魂斷藍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男女主角的外型都是完美無瑕的,那種美與優雅非常吸引我。」曹導提起了年少時期在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電影時,雙眼靈活地轉動著,如同少年般,煥發出熱切純真的光芒。
「除了《魂斷藍橋》,我覺得生命中有很多安排,都一點一滴地讓你走向某個方向。其實,我畢業時是想要做攝影的,但那時『太陽系』MTV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店裡有很多影碟可以看外國電影,我就看到了一部電影。」曹導說。
「《魂斷威尼斯》?」我斗膽揣測。
「對!就是《魂斷威尼斯》。那部電影打開了我的新世界,我還記得故事是講述一個老人對一個青春男子的眷戀與遺憾。那部電影讓我開始覺得,攝影只是一個媒介,導演好像真正可以講故事。」曹導回憶著邁向導演之路的初心,感性地說。
接著,曹導述說起就讀世新大學的往事。當時,好友因找不到他而在桌上留下一本白先勇的《台北人》,從此翻轉了他的人生,讓他從一個不愛讀書、四肢發達的運動男孩蛻變成了纖細敏感的藝文青年。幾年的時光荏苒流逝了,畢業後的曹導進入影視行業後,某次在因緣際會下獲得了與公視合拍電視劇的機會,便主動提出希望將白先勇的《孽子》改編成電視劇,卻因為同志題材在當時較為敏感而遭到拒絕。想不到,一個禮拜之後,曹導在餐廳巧遇了白先勇,便主動向他表明了有意拍攝《孽子》的想法。當時,白先勇與曹導約定三天後再碰頭。那段期間,曹導向公視高層提出了《孽子》值得一拍的理由,與此同時,白先勇也因看了女同志題材人生劇展《童女之舞》,認為他能夠處理《孽子》的細膩情感,因而點頭答應。
聽見曹導的這番話,感覺彷彿有無形的命運之手,將《孽子》交付給了他,而他也不負眾望,將《孽子》轉化成同志影視題材的經典之作。2003年,台灣舉辦了華語圈首屆的同志遊行,當年《孽子》的播出,也在台灣引起了極為強烈的轟動與反響。我深信《孽子》以影像的力量,推波助瀾地促進了台灣同志平權的發展,曹導的選材目光,精準得不可思議!想到這裡,我試圖更深入地探索,曹導創作的養成,動機與脈絡。
對人、對生命的悲憫
侯:我想,在台灣的七零至八零年代,是台灣文化非常具衝擊性的年代,不僅有鄉土文學論戰、本土意識的崛起,還有最重要的,風起雲湧的台灣電影新浪潮,這樣的浪潮貫穿了您的青年年代,在這樣的氛圍裡成長,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體驗?那段歲月是否影響了您的創作?
曹:我覺得這只是一種幸運吧!那個年代可以說是台灣文藝復興的年代。我相信台灣這兩三年又會是一個文藝復興,因為經濟又起飛了,文藝的活動力又會起來。其實回顧台灣電影新浪潮,當時真正受惠的是侯孝賢、楊德昌這批新浪潮的先鋒導演,這樣的浪潮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意義就是有一個養分,然而當我們想要大展身手的時候,整個產業已經往下掉了。
我覺得民歌影響台灣非常大,因為台灣文化思維的改變,民歌是第一聲槍響。民歌之後才有所謂的新文學、法國電影新浪潮、存在主義,直到台灣電影新浪潮的崛起,開始有一種文藝青年的思維。然而台灣新電影的影響,到後來慢慢變成一種包袱,尤其在我拍《孽子》的那段時間,甚至拍人生劇展、進到這個產業開始當導演的時候,台灣的藝術與商業電影已經決裂了,侯導與朱延平雙方的電影創作理念已經完全不相容了。後來的台灣電影因為票房因素逐漸下滑,國際對藝術電影的關注慢慢轉向中國,所以就有了中國第五代導演,例如張藝謀、陳凱歌等等,而台灣的影視產業也慢慢沉寂了。
侯:台灣新電影不就是意味著對舊時代電影的叛逆與創新,為何會形成所謂的包袱呢?
曹:所謂的包袱是說,我們這一批人因為受到那個時代的影響,一直堅持一種文藝的、藝術性的說故事,可是那時候已經很辛苦了。與我同一時期的還有蔡明亮與張作驥,但他們就是完全走向電影。我一開始是攝影師,那時我走向了劇情片,而我早就看過那些經典藝術電影。對我來說,電影是最後的冠冕,不是隨便就可以去摘的,所以我慢慢拍,不急著走向電影。但後來我認為只要是影像都一樣,現在的我反而想拍什麼就拍,根本沒有太多的壓力和包袱。
侯:綜觀曹導整體創作的脈絡與安排,可以發現您反響更大的作品,往往是較具有年代感的故事。這些故事都牽涉到遷移的主題,從中國遷移到台灣的小人物,受盡了磨難,也包含社會價值觀的衝突與自我理想的衝突,例如《孤戀花》。而您這一輩與王童也不是同一輩的導演,但您又敏銳地捕捉了那個時代的感覺,我私心覺得《孤戀花》的演員表現堪稱完美,更何況您的養成又是屬於新電影,與本土意識崛起的年代,為何會有這樣的反差呢?
曹:這的確很奇怪,拍《孤戀花》時,我才四十初頭,當時演員們看到我本人,都很訝異我竟然不是六、七十歲的老頭。影響我很大的,其實是在我開始自詡為文藝青年的時候,所讀到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同樣是大時代的浪濤下,小人物的愛情故事。我忽然發現,有史詩格局氣魄的東西都發生在戰亂、顛沛流離的年代。後來想拍《孤戀花》也是因為如此,再加上女性同志的情誼,在那個時代又是更不可能的狀態,於是很想將女性的纖細情感給架構出來。
本來我是想拍電影,但白老師說:「《孽子》那麼成功,我們再拍個電視劇啦!」其實我拍《孤戀花》也是為了練功,考驗自己能不能詮釋好女性的情感。因為在我很小時,我爸就過世了,我跟著我媽和三個姊姊一起長大,小時候還會跟著姊姊打毛線,她們甚至會把我裝扮成女性,真的是很特別的成長經驗。我在情感上也比較中性,我覺得不管男女,都有脆弱纖細的一面。
侯:您的作品《童女之舞》、《孽子》與《孤戀花》都是屬於同志題材,是因為同志在過往的年代裡不被接受,與社會價值觀的衝突性更大嗎?
曹:可能就是那種被隔絕的感覺吧!我小時候是在學校操場長大的……
侯:我想,在台灣的七零至八零年代,是台灣文化非常具衝擊性的年代,不僅有鄉土文學論戰、本土意識的崛起,還有最重要的,風起雲湧的台灣電影新浪潮,這樣的浪潮貫穿了您的青年年代,在這樣的氛圍裡成長,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體驗?那段歲月是否影響了您的創作?
曹:我覺得這只是一種幸運吧!那個年代可以說是台灣文藝復興的年代。我相信台灣這兩三年又會是一個文藝復興,因為經濟又起飛了,文藝的活動力又會起來。其實回顧台灣電影新浪潮,當時真正受惠的是侯孝賢、楊德昌這批新浪潮的先鋒導演,這樣的浪潮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意義就是有一個養分,然而當我們想要大展身手的時候,整個產業已經往下掉了。
我覺得民歌影響台灣非常大,因為台灣文化思維的改變,民歌是第一聲槍響。民歌之後才有所謂的新文學、法國電影新浪潮、存在主義,直到台灣電影新浪潮的崛起,開始有一種文藝青年的思維。然而台灣新電影的影響,到後來慢慢變成一種包袱,尤其在我拍《孽子》的那段時間,甚至拍人生劇展、進到這個產業開始當導演的時候,台灣的藝術與商業電影已經決裂了,侯導與朱延平雙方的電影創作理念已經完全不相容了。後來的台灣電影因為票房因素逐漸下滑,國際對藝術電影的關注慢慢轉向中國,所以就有了中國第五代導演,例如張藝謀、陳凱歌等等,而台灣的影視產業也慢慢沉寂了。
侯:台灣新電影不就是意味著對舊時代電影的叛逆與創新,為何會形成所謂的包袱呢?
曹:所謂的包袱是說,我們這一批人因為受到那個時代的影響,一直堅持一種文藝的、藝術性的說故事,可是那時候已經很辛苦了。與我同一時期的還有蔡明亮與張作驥,但他們就是完全走向電影。我一開始是攝影師,那時我走向了劇情片,而我早就看過那些經典藝術電影。對我來說,電影是最後的冠冕,不是隨便就可以去摘的,所以我慢慢拍,不急著走向電影。但後來我認為只要是影像都一樣,現在的我反而想拍什麼就拍,根本沒有太多的壓力和包袱。
侯:綜觀曹導整體創作的脈絡與安排,可以發現您反響更大的作品,往往是較具有年代感的故事。這些故事都牽涉到遷移的主題,從中國遷移到台灣的小人物,受盡了磨難,也包含社會價值觀的衝突與自我理想的衝突,例如《孤戀花》。而您這一輩與王童也不是同一輩的導演,但您又敏銳地捕捉了那個時代的感覺,我私心覺得《孤戀花》的演員表現堪稱完美,更何況您的養成又是屬於新電影,與本土意識崛起的年代,為何會有這樣的反差呢?
曹:這的確很奇怪,拍《孤戀花》時,我才四十初頭,當時演員們看到我本人,都很訝異我竟然不是六、七十歲的老頭。影響我很大的,其實是在我開始自詡為文藝青年的時候,所讀到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同樣是大時代的浪濤下,小人物的愛情故事。我忽然發現,有史詩格局氣魄的東西都發生在戰亂、顛沛流離的年代。後來想拍《孤戀花》也是因為如此,再加上女性同志的情誼,在那個時代又是更不可能的狀態,於是很想將女性的纖細情感給架構出來。
本來我是想拍電影,但白老師說:「《孽子》那麼成功,我們再拍個電視劇啦!」其實我拍《孤戀花》也是為了練功,考驗自己能不能詮釋好女性的情感。因為在我很小時,我爸就過世了,我跟著我媽和三個姊姊一起長大,小時候還會跟著姊姊打毛線,她們甚至會把我裝扮成女性,真的是很特別的成長經驗。我在情感上也比較中性,我覺得不管男女,都有脆弱纖細的一面。
侯:您的作品《童女之舞》、《孽子》與《孤戀花》都是屬於同志題材,是因為同志在過往的年代裡不被接受,與社會價值觀的衝突性更大嗎?
曹:可能就是那種被隔絕的感覺吧!我小時候是在學校操場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