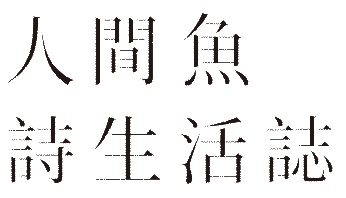流浪的魚,乘著四季的血肉前進
專訪 鄭琬融
訪談 | PS.黃觀
文字編輯 | 郭瀅瀅
攝影 | 郭潔渝
文字編輯 | 郭瀅瀅
攝影 | 郭潔渝
鄭琬融,民國90年後出生的世代,近期剛出版第一本個人詩集《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會注意到她,是在網路上,看到她將自己的詩作,透過朗讀與影像來創作影像詩,引起正在籌拍詩電影的我的好奇。
約訪的當天,她剛結束白天的編輯工作,直接與男友一起赴約。雖然臉龐有一些下班後的疲憊,但是談起詩、創作,所閃現的笑容仍是明亮、充滿生命力。在訪談裡,她並不諱言任何話題,談過往經歷、談曾有的困境與心境轉換。書寫是她療癒自我的過程,也是生命經驗的紀實。
約訪的當天,她剛結束白天的編輯工作,直接與男友一起赴約。雖然臉龐有一些下班後的疲憊,但是談起詩、創作,所閃現的笑容仍是明亮、充滿生命力。在訪談裡,她並不諱言任何話題,談過往經歷、談曾有的困境與心境轉換。書寫是她療癒自我的過程,也是生命經驗的紀實。
得獎,像是走到了岔路口
黃:妳跟魚有緣,我們是人間魚詩生活誌,遊戲的人,思考的魚。妳的臉書名叫bleedingocean,在2016年獨立出版詩冊《一些流浪的魚》,我們的訪談裡,想請妳談談詩、妳的兩本詩集,談談妳自己、自己與詩的關係。首先,妳在2020年以《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獲得第七屆楊牧詩獎,請妳談談這事是怎麼發生的?得這個獎對妳的意義,得獎前後,有什麼不同?
鄭:在投稿這一屆楊牧詩獎前,其實已經投過紅樓詩獎與前一屆的楊牧詩獎,但因為作品尚不夠成熟,也還未有如何整理整本詩集、分輯等等的概念,所以一直不斷地在進行修改。可以說得了這個獎有點像是我對這本詩集的想像終於成形了吧。至於得獎前後,除了我得以把獎金拿去償還出國交換時所借的錢外,似乎沒什麼改變,還是繼續地在創作。而得這個獎的意義對我來說,像是走到了某種岔路口,總感覺要更認真創作才對得起這個獎項。
黃:《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得獎後,為什麼由木馬文化出版?妳也在這裡擔任外文編輯,每天上下班,喜歡這份工作嗎?編輯工作帶給妳什麼?
鄭:其實有收到出版社的邀約,所以就在自己任職的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擔任的這份編輯工作自己滿喜歡的,雖然編輯比較多面對的是溝通與協調的部分,不過其中能夠閱讀小說的時候,還是覺得自己挺幸運。仍然可以閱讀新的東西,深入作品思考,這讓我還是能夠保持著創作的渴望。以前大學看書,比較多是看完就轉往下一本,不過因為編輯的工作,常常看個三、四次,就更讓我會去想一本書的核心是什麼,以及一個作家的信念與特色等等,這些比較全面的事情,不是只單看一本作品。
黃:妳跟魚有緣,我們是人間魚詩生活誌,遊戲的人,思考的魚。妳的臉書名叫bleedingocean,在2016年獨立出版詩冊《一些流浪的魚》,我們的訪談裡,想請妳談談詩、妳的兩本詩集,談談妳自己、自己與詩的關係。首先,妳在2020年以《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獲得第七屆楊牧詩獎,請妳談談這事是怎麼發生的?得這個獎對妳的意義,得獎前後,有什麼不同?
鄭:在投稿這一屆楊牧詩獎前,其實已經投過紅樓詩獎與前一屆的楊牧詩獎,但因為作品尚不夠成熟,也還未有如何整理整本詩集、分輯等等的概念,所以一直不斷地在進行修改。可以說得了這個獎有點像是我對這本詩集的想像終於成形了吧。至於得獎前後,除了我得以把獎金拿去償還出國交換時所借的錢外,似乎沒什麼改變,還是繼續地在創作。而得這個獎的意義對我來說,像是走到了某種岔路口,總感覺要更認真創作才對得起這個獎項。
黃:《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得獎後,為什麼由木馬文化出版?妳也在這裡擔任外文編輯,每天上下班,喜歡這份工作嗎?編輯工作帶給妳什麼?
鄭:其實有收到出版社的邀約,所以就在自己任職的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擔任的這份編輯工作自己滿喜歡的,雖然編輯比較多面對的是溝通與協調的部分,不過其中能夠閱讀小說的時候,還是覺得自己挺幸運。仍然可以閱讀新的東西,深入作品思考,這讓我還是能夠保持著創作的渴望。以前大學看書,比較多是看完就轉往下一本,不過因為編輯的工作,常常看個三、四次,就更讓我會去想一本書的核心是什麼,以及一個作家的信念與特色等等,這些比較全面的事情,不是只單看一本作品。
詩,為自己帶來沉澱與鍛鍊
黃:2016年妳獨立出版詩冊《一些流浪的魚》,妳說:「為了能將死去的皮脫除乾淨,讓芽繼續萌發,是乎有了這本詩冊的誕生」。妳的詩似乎與妳的生命經驗是在一起的,從這本詩冊到現在這本,妳的生命經驗有什麼轉變?詩扮演了什麼角色?
鄭:在寫《一些流浪的魚》這本小詩冊時,我對創作的主題還在摸索,從最早大家都寫的愛情,到後來思考的身體、城市與偏鄉等等,可以說有些後來想寫的東西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萌發出來吧。當書寫開始,我對這些主題或者經驗的感受才得以一一釐清。從出版《一些流浪的魚》到現在,也已經過了近五年,無論是我對於自己的厭惡感、女性經驗、在城市與偏鄉之間移動,甚至前往異域,這些東西都已經讓我變得不大一樣了。詩在我生命之中的位置,除了讓我沉澱自己,更督促著我要鍛鍊一種新的眼光去感受這個世界。不覺得這種鍛鍊很有趣嗎?這種隨時保持對於世界的新鮮感,也是為什麼詩一直吸引我的地方。
黃:妳認不認為妳是一個詩人?妳怎麼看待身為一個詩人?
鄭:我覺得,我算是一個詩人吧,都已經出版一本詩集了。不過,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創作者或者是寫作者,我會希望寫其他的東西。我覺得詩人都有一個特質是,可以察覺到一句話的某個字或者某個詞稍微一改動,或者形容詞、語氣稍微一改動,就能夠擁有怎樣的差別與影響,也就是語言上的評量,會知道一句話要如何能說得更好或更有力量。
黃:請談談妳的寫詩經歷,怎麼會成為一個詩人的?
鄭:或許是個意外吧。沒有特別想過要成為詩人,只是一次小學被稱讚寫得不錯,就一直繼續寫下去了。比較特別的轉捩點是,在高中我遇到了耕莘青年寫作會的一群寫作夥伴,這才讓我更了解現代詩的面目,而不是只侷限於課本上。在得知語言可以如此有趣後,我才算是真的愛上詩這個文體吧。就這樣懵懵懂懂地寫到今天。
黃:2016年妳獨立出版詩冊《一些流浪的魚》,妳說:「為了能將死去的皮脫除乾淨,讓芽繼續萌發,是乎有了這本詩冊的誕生」。妳的詩似乎與妳的生命經驗是在一起的,從這本詩冊到現在這本,妳的生命經驗有什麼轉變?詩扮演了什麼角色?
鄭:在寫《一些流浪的魚》這本小詩冊時,我對創作的主題還在摸索,從最早大家都寫的愛情,到後來思考的身體、城市與偏鄉等等,可以說有些後來想寫的東西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萌發出來吧。當書寫開始,我對這些主題或者經驗的感受才得以一一釐清。從出版《一些流浪的魚》到現在,也已經過了近五年,無論是我對於自己的厭惡感、女性經驗、在城市與偏鄉之間移動,甚至前往異域,這些東西都已經讓我變得不大一樣了。詩在我生命之中的位置,除了讓我沉澱自己,更督促著我要鍛鍊一種新的眼光去感受這個世界。不覺得這種鍛鍊很有趣嗎?這種隨時保持對於世界的新鮮感,也是為什麼詩一直吸引我的地方。
黃:妳認不認為妳是一個詩人?妳怎麼看待身為一個詩人?
鄭:我覺得,我算是一個詩人吧,都已經出版一本詩集了。不過,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創作者或者是寫作者,我會希望寫其他的東西。我覺得詩人都有一個特質是,可以察覺到一句話的某個字或者某個詞稍微一改動,或者形容詞、語氣稍微一改動,就能夠擁有怎樣的差別與影響,也就是語言上的評量,會知道一句話要如何能說得更好或更有力量。
黃:請談談妳的寫詩經歷,怎麼會成為一個詩人的?
鄭:或許是個意外吧。沒有特別想過要成為詩人,只是一次小學被稱讚寫得不錯,就一直繼續寫下去了。比較特別的轉捩點是,在高中我遇到了耕莘青年寫作會的一群寫作夥伴,這才讓我更了解現代詩的面目,而不是只侷限於課本上。在得知語言可以如此有趣後,我才算是真的愛上詩這個文體吧。就這樣懵懵懂懂地寫到今天。
死亡,曾是心裡低迴的命題
黃:談談詩集為什麼取名為《一些流浪的魚》?為什麼是「魚」這個意象?
鄭:這本小詩冊是大約二十歲的時候,覺得可以給出的東西,大概有二十首詩。因為沒有經過排列,各自散在一些不同的時期,所以叫做一些流浪的魚。
魚給我的意象是比較黏膩的,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魚。因為家裡以前養過的魚,都比較容易生病,容易長一些黴菌。所以魚對我來說,像是一種尷尬的存在,會讓我不舒服,但是偶爾在某個層面又會想起,有點像那個時候「死」給我的感覺。
黃:在這本詩集裡,除了是比較憂鬱的狀態之外,「海」對妳有很大的影響嗎?為什麼喜歡海的意象?
鄭:我在海邊看日落的時候,會覺得太陽一直在流血到海裡。我以前會覺得海是可以容納所有的東西的地方,而且以前出去玩的時候,我爸也都會帶我們去海邊。海有點像是一個可以逃離都市及生活的混亂會去到的地方,也是一個可以放鬆或者是把東西丟進去、心情不好可以去的地方。除此之外,我看到海會想到一些負面的東西,但到了最近,在《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這本詩集出版前,海不會再讓我想到死亡。到現在看到海的時候,海又可以讓我有一些不同的聯想。
黃:妳剛剛多次提到在某些時候,妳會想到或意識到「死亡」。談談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鄭:大概是大學前半部的時候,我可以說我滿憂鬱的,或者是處於一些比較不安的狀況。19歲當時我常失眠,幾乎都天亮才睡。去醫院做診斷、抽血,才知道我有甲狀腺亢進,所以一直服藥到現在,前陣子才剛停。我的狀況需要吃藥,因為它影響到內分泌或者是心悸等症狀,影響許多層面。所以我會想到死亡,可能就是跟我當時的狀況與意識型態有關。但是漸漸地,當我能離開這種狀態之後,注意力就不一定會在我自己,也比較有能力去思考別的事情,比方說對環境的看法、城市與鄉下的差異等。
黃:談談詩集為什麼取名為《一些流浪的魚》?為什麼是「魚」這個意象?
鄭:這本小詩冊是大約二十歲的時候,覺得可以給出的東西,大概有二十首詩。因為沒有經過排列,各自散在一些不同的時期,所以叫做一些流浪的魚。
魚給我的意象是比較黏膩的,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魚。因為家裡以前養過的魚,都比較容易生病,容易長一些黴菌。所以魚對我來說,像是一種尷尬的存在,會讓我不舒服,但是偶爾在某個層面又會想起,有點像那個時候「死」給我的感覺。
黃:在這本詩集裡,除了是比較憂鬱的狀態之外,「海」對妳有很大的影響嗎?為什麼喜歡海的意象?
鄭:我在海邊看日落的時候,會覺得太陽一直在流血到海裡。我以前會覺得海是可以容納所有的東西的地方,而且以前出去玩的時候,我爸也都會帶我們去海邊。海有點像是一個可以逃離都市及生活的混亂會去到的地方,也是一個可以放鬆或者是把東西丟進去、心情不好可以去的地方。除此之外,我看到海會想到一些負面的東西,但到了最近,在《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這本詩集出版前,海不會再讓我想到死亡。到現在看到海的時候,海又可以讓我有一些不同的聯想。
黃:妳剛剛多次提到在某些時候,妳會想到或意識到「死亡」。談談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鄭:大概是大學前半部的時候,我可以說我滿憂鬱的,或者是處於一些比較不安的狀況。19歲當時我常失眠,幾乎都天亮才睡。去醫院做診斷、抽血,才知道我有甲狀腺亢進,所以一直服藥到現在,前陣子才剛停。我的狀況需要吃藥,因為它影響到內分泌或者是心悸等症狀,影響許多層面。所以我會想到死亡,可能就是跟我當時的狀況與意識型態有關。但是漸漸地,當我能離開這種狀態之後,注意力就不一定會在我自己,也比較有能力去思考別的事情,比方說對環境的看法、城市與鄉下的差異等。
透過聲音,文字有了續命的方式
黃:在網路上看到妳有多首的影像詩,多由妳自己朗誦,讀者對妳的聲音並不陌生。影像詩有音聲、影像、文字,妳對這三者的關係及影像詩,有什麼看法或期待?妳對影像詩與純文字有什麼不同,哪些詩妳會想要作成影像詩?又妳知道詩電影嗎?認為那應該是什麼?
鄭:當以聲音將詩念出,這些文字就彷彿擁有了另一種可以捉住的、可以續命的方式重新存在了一次。每個人的聲腔不同,在意的句子、希望重複或朗誦的語調也不同,呈現出來的感受自然也就不一樣……
黃:在網路上看到妳有多首的影像詩,多由妳自己朗誦,讀者對妳的聲音並不陌生。影像詩有音聲、影像、文字,妳對這三者的關係及影像詩,有什麼看法或期待?妳對影像詩與純文字有什麼不同,哪些詩妳會想要作成影像詩?又妳知道詩電影嗎?認為那應該是什麼?
鄭:當以聲音將詩念出,這些文字就彷彿擁有了另一種可以捉住的、可以續命的方式重新存在了一次。每個人的聲腔不同,在意的句子、希望重複或朗誦的語調也不同,呈現出來的感受自然也就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