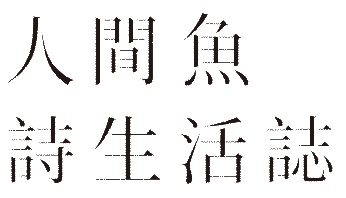少年鸚鵡 維持的社交距離
文|郭瀅瀅
遙望的山,渡假的海:我海馬迴裡低吟的,山海誌
身為一個從小居住在城市,而且是一個只要太忙碌,少吃一頓餐就氣血虛弱的女性,山與海在我的經驗裡是疏離的,甚至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危險象徵。因為它在我心裡,不是以觀光為目的去靠近的景點,或淺嚐即止下所認識的山海意象,而是亙古以來就存在著,未經現代開墾而有著原始樣貌的山、距離陸地遙遠的海。
過去原住民真實生活在其中的那種山。
燈塔看守員、航海者接觸的那種海。
那是不可測的神秘,有著狂暴與寂止的兩極性。
我的登山經驗幾乎是零。
如果步行那種海拔很低,空氣還未稀薄的小小登山步道不算的話。
因為曾經著迷那些攀登高海拔山峰的電影與報導文學,當有人說出山這個詞,在我心裡首先浮現的,總是聖母峰,以及攀登聖母峰的人。透過他們,我窺見了那無法親自經驗的美麗地貌,而看見他們依循著一股內在熱情而奔向未知,絲毫不怕可能面臨的斷崖與絕境,既替他們捏一把冷汗,又有著一種親自冒險的投射與想像。
高海拔的山,有時晴朗無風,有時又可能突然降起大雪。身在其中,人的一切都好渺小,生死,好像也由它來決定。此時,山經常被說是殘酷,正如大自然經常被貼上殘酷這個標籤。但山不殘酷,只是「是它所是」,是它所是地,繼續著它的運行,不論你是否性命垂危,山就是山。就像宮崎駿動畫裡的山神,祂只是純粹地「在」,因此祂從不干涉、沒有要維持正義或替誰復仇,也沒有符合人所期待地去拯救任何一方。祂只是看著。
這也如同海。
海就是海。
對歐洲海中礁島上的燈塔看守者而言,海不浪漫。
海是深沉的呼嘯聲。
巨浪隨時會吞噬整座燈塔。他不能探頭看海,否則會被捲進海裡。
正因為心裡的山與海,它的美麗包含著它的生猛,
我所嚮往的山,是遙望的山。
或是,在山裡可以過著城市生活一般的山。
我所嚮往的海,是渡假的海。
是在陽光下可以看見白色浪花,夜晚可以聽見海浪拍打岩石,發出輕快聲響的海。
這是都市人如我,海馬迴裡低吟的,山海誌。
身為一個從小居住在城市,而且是一個只要太忙碌,少吃一頓餐就氣血虛弱的女性,山與海在我的經驗裡是疏離的,甚至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危險象徵。因為它在我心裡,不是以觀光為目的去靠近的景點,或淺嚐即止下所認識的山海意象,而是亙古以來就存在著,未經現代開墾而有著原始樣貌的山、距離陸地遙遠的海。
過去原住民真實生活在其中的那種山。
燈塔看守員、航海者接觸的那種海。
那是不可測的神秘,有著狂暴與寂止的兩極性。
我的登山經驗幾乎是零。
如果步行那種海拔很低,空氣還未稀薄的小小登山步道不算的話。
因為曾經著迷那些攀登高海拔山峰的電影與報導文學,當有人說出山這個詞,在我心裡首先浮現的,總是聖母峰,以及攀登聖母峰的人。透過他們,我窺見了那無法親自經驗的美麗地貌,而看見他們依循著一股內在熱情而奔向未知,絲毫不怕可能面臨的斷崖與絕境,既替他們捏一把冷汗,又有著一種親自冒險的投射與想像。
高海拔的山,有時晴朗無風,有時又可能突然降起大雪。身在其中,人的一切都好渺小,生死,好像也由它來決定。此時,山經常被說是殘酷,正如大自然經常被貼上殘酷這個標籤。但山不殘酷,只是「是它所是」,是它所是地,繼續著它的運行,不論你是否性命垂危,山就是山。就像宮崎駿動畫裡的山神,祂只是純粹地「在」,因此祂從不干涉、沒有要維持正義或替誰復仇,也沒有符合人所期待地去拯救任何一方。祂只是看著。
這也如同海。
海就是海。
對歐洲海中礁島上的燈塔看守者而言,海不浪漫。
海是深沉的呼嘯聲。
巨浪隨時會吞噬整座燈塔。他不能探頭看海,否則會被捲進海裡。
正因為心裡的山與海,它的美麗包含著它的生猛,
我所嚮往的山,是遙望的山。
或是,在山裡可以過著城市生活一般的山。
我所嚮往的海,是渡假的海。
是在陽光下可以看見白色浪花,夜晚可以聽見海浪拍打岩石,發出輕快聲響的海。
這是都市人如我,海馬迴裡低吟的,山海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