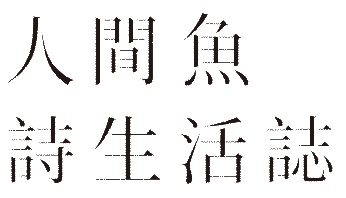手
文|郭瀅瀅
「花瓣是丑角,花莖由下方黑色空洞升起。我握著一枝花莖在手中,我是那花莖」。紅墨水在輕觸紙張的瞬間滲出,我延展著它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停頓,化為血滴般的混濁圓點。我放下筆,闔上吳爾芙的《海浪》。
在每一個感受飽滿的瞬間,退出書本,面向窗外。
花朵在凌亂的公園裡搖曳,流浪者在垃圾桶前俯身,雙手向下翻找,抽出了一盒雞骨外露的便當和歪曲的圓形餐盒。他搖晃凹陷的圓形,確認裡頭是否有食物,附近的比丘尼或扮裝的尼姑正化緣,走走停停。手捧著缽,沿路向公園裡的路人鞠躬,唯獨跳過了流浪者。他不在能夠給予的行列。
窗外下起了雨。白色的花承受不住雨水的抖落而越趨矮小。
流浪者攤開掌心,雙手併攏,承接飄進手裡的雨水,抹了抹自己灰白的長髮。目光空洞,臉上宿命的氣息說著,自己也僅只是被浪推到了這裡,再也沒有回返的可能,卻也彷彿,不再有更大的苦難能凌駕於他。彷彿,在第一次躺臥街上的時候也是他第一次放下。
雨勢加劇,輕薄的花也無處可躲,彎起它綠色的身子靠近它的根。
尼姑將手裡的缽收進背包,沿著屋簷快步走去。
流浪者在大雨中緩緩走著,直到背影朦朧。
我感覺哀傷。也許不幸一點,也會成為這樣的背影,卻未必能坦然如他。
差點流落街頭的恐懼,還在意識的深處隱隱環繞。
年少,像一隻被丟進陌生空間的昆蟲,空氣稀薄,沒有花葉可攀附。站不穩,也飛不高,分不清是對飛行不熟練,還是自身的平衡系統出了問題,或僅是振翅得不夠快速而一再跌倒。迴旋於牆邊。
反覆遷移。容身處越趨窄小而捨棄的,象徵中產的物,在它曾經所處的空間裡,成為若有似無的殘影。古典鋼琴年久失修,走音,成為一堵棗紅色的牆,充當浴室與客梯廳的隔間,吸收所有的濕氣。從此,物質在心裡便多了一份尷尬。置身於物又無法真正與任何一物連結。擁有的同時又在物與物之間微微喘息。它無法是我的歸處。
渴望睡眠。
睡眠的時候氣息最穩。
而在夜晚更深的呼吸之前,無數次以枕頭巾的銳角摩擦指節的側面,反覆掐緊直到與它密不可透地貼合,手不再有施力的空間。
世界剩下手與痛,剩下手裡的事物。
掐緊的傷痕在皮膚表面增生肥厚的組織,當有人牽起我的手無意間碰到一處堅硬的表皮,並以他困惑的手指反覆探測,彷彿它與細嫩不該並存似的,我說,黏稠的裂縫早已長成堅硬的脈絡,在硬處的上頭無論如何刮搔都無關痛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