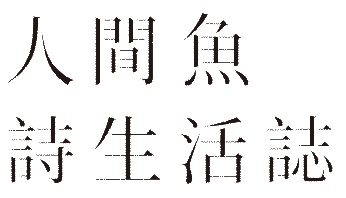昨日的凝視
文|郭瀅瀅
1. 麻雀
那天下午,我在街道上看見一隻死去的麻雀。牠仰躺著,身體沒有明確的缺損或變形,不像是曾被捕食或遭受撞擊的樣子。也許,只是因為生病而從樹梢上掉了下來,便沒有力氣再飛。牠的精神已經遠走,身體卻仍在地面上經受著烈日,而腹部的細毛也還泛著油亮的光澤,彷彿尚未知曉死亡,或是,晚一步才會與死亡同步。我想像一個哀傷的小孩一樣埋葬牠,卻躊躇不前,為著自己也不清楚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在牠靜止的身軀裡,撞見了永恆的寧靜而不知所措。
當我決定遠去,視線卻還掛記著牠。回頭間,一雙雙倉促的腳重重踩踏,我彷彿將要聽見骨骼碎裂的微細聲響。最後,牠在一個陌生男子的黑皮鞋間翻滾了起來,騰空,像是一個不曾有過生命,被擺放得太久而即將裂解的,毽子,在旋轉飛舞的瞬間落下了一半的羽毛。而牠並沒有亂了他的步伐,是步伐改變了牠的方向。
當皮鞋遠去,我想起了那隻被豢養了太久,不再歌唱的橘紅色金絲雀。童年的某個下午,牠振翅飛出了窗外卻落入了野狗的口中。兒時的我站在窗前,錯愕而愧疚著。後來我經常仰望樹梢,希望能無意間撞見牠的靈魂。
也許,永恆寧靜的一切總以闕如的面貌,撞擊著我的心。
2. 木槿
那天清晨,木槿終於開花了。橘紅色的花瓣乾燥而薄透,我凝視得出神,它像是一張被精工雕琢好的紙,上面有著微細的皺摺。也許那是它在展開之前,在窄小的花萼裡折疊著自身的痕跡,而它將隨著時間,成為一道道深邃的裂縫。
大雨落下,我決定將它收藏在影像裡。不寫實再現它與它的周圍,彷彿它是一個雨中獨自冥想,超越了物種界定的存在,僅以花朵的樣貌混淆我的認知。而那細長的花蕊在色澤最深的中心裡,向外伸出,感知著我無法知道的訊息。
雨加速了生命的循環。在雨之後,它闔起了自身,絨毛狀的花蕊也逐漸靠近濕潤的花瓣。那是它們最靠近彼此的時候。但也許,它們僅是回到了綻放以前,在無法伸展的空間裡,未成形而彼此依偎的隱密狀態。
它終究是回到了濕潤裡,混合著雨水與自身的水分,縮小而聚攏。我不再能看見它的內部,而它從此成了我的夢境。在無數次的午睡裡,巨大的花瓣在意識混沌之時顯現在眼前,並緩慢推進,我分不清楚是它在靠近我,或是我走進它。而當我感覺正進入它的中心時,往往也瞬間醒來。
那廣大、渲染著視線的內部色彩,也就蔓延進了我的日常。深邃而接近黑色的紅、明亮而濃郁的黃——那是睜開眼睛以前,預示著心象黑幕即將落下的,最後一瞬。於是在日常裡,透過肉眼侷限所看見的客觀樣貌,漸漸在我心裡微小了起來。
那天下午,我在街道上看見一隻死去的麻雀。牠仰躺著,身體沒有明確的缺損或變形,不像是曾被捕食或遭受撞擊的樣子。也許,只是因為生病而從樹梢上掉了下來,便沒有力氣再飛。牠的精神已經遠走,身體卻仍在地面上經受著烈日,而腹部的細毛也還泛著油亮的光澤,彷彿尚未知曉死亡,或是,晚一步才會與死亡同步。我想像一個哀傷的小孩一樣埋葬牠,卻躊躇不前,為著自己也不清楚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在牠靜止的身軀裡,撞見了永恆的寧靜而不知所措。
當我決定遠去,視線卻還掛記著牠。回頭間,一雙雙倉促的腳重重踩踏,我彷彿將要聽見骨骼碎裂的微細聲響。最後,牠在一個陌生男子的黑皮鞋間翻滾了起來,騰空,像是一個不曾有過生命,被擺放得太久而即將裂解的,毽子,在旋轉飛舞的瞬間落下了一半的羽毛。而牠並沒有亂了他的步伐,是步伐改變了牠的方向。
當皮鞋遠去,我想起了那隻被豢養了太久,不再歌唱的橘紅色金絲雀。童年的某個下午,牠振翅飛出了窗外卻落入了野狗的口中。兒時的我站在窗前,錯愕而愧疚著。後來我經常仰望樹梢,希望能無意間撞見牠的靈魂。
也許,永恆寧靜的一切總以闕如的面貌,撞擊著我的心。
2. 木槿
那天清晨,木槿終於開花了。橘紅色的花瓣乾燥而薄透,我凝視得出神,它像是一張被精工雕琢好的紙,上面有著微細的皺摺。也許那是它在展開之前,在窄小的花萼裡折疊著自身的痕跡,而它將隨著時間,成為一道道深邃的裂縫。
大雨落下,我決定將它收藏在影像裡。不寫實再現它與它的周圍,彷彿它是一個雨中獨自冥想,超越了物種界定的存在,僅以花朵的樣貌混淆我的認知。而那細長的花蕊在色澤最深的中心裡,向外伸出,感知著我無法知道的訊息。
雨加速了生命的循環。在雨之後,它闔起了自身,絨毛狀的花蕊也逐漸靠近濕潤的花瓣。那是它們最靠近彼此的時候。但也許,它們僅是回到了綻放以前,在無法伸展的空間裡,未成形而彼此依偎的隱密狀態。
它終究是回到了濕潤裡,混合著雨水與自身的水分,縮小而聚攏。我不再能看見它的內部,而它從此成了我的夢境。在無數次的午睡裡,巨大的花瓣在意識混沌之時顯現在眼前,並緩慢推進,我分不清楚是它在靠近我,或是我走進它。而當我感覺正進入它的中心時,往往也瞬間醒來。
那廣大、渲染著視線的內部色彩,也就蔓延進了我的日常。深邃而接近黑色的紅、明亮而濃郁的黃——那是睜開眼睛以前,預示著心象黑幕即將落下的,最後一瞬。於是在日常裡,透過肉眼侷限所看見的客觀樣貌,漸漸在我心裡微小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