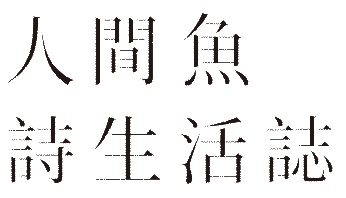未完成的小說
文|郭瀅瀅
1.
她的雙頰泛著紅暈,手臂的內側微微透出浮起的血管。像是一張透光的紙,單薄得容易破掉。也許她的美與神聖,正是因著生命的脆弱性而來的。而當她躺在黑色的棺木裡,成為靜物般的存在時,我才注意到她如此窄小。也許,僅是因為她身上那些令人嚮往的美好事物,在硬冷的長方形裡,瞬間失去了價值。
從那一刻起,我彷彿成了一面不忠實的鏡子,在美好的事物面前,心裡總是浮現凋零的樣貌。而他——從認識的最初就一再向我說——他永遠帶不走任何喜愛的事物,包括我。「有一天,我也將離開妳。」那一次在擁抱過後,他落下了淚來。我第一次看見他哭。而他似乎與我有著不同的質地,因此哭的方式也與我不同。
我的淚水經常像洪水般不受控制,伴隨著身體的顫抖,那些無法言說的感受,在一瞬之間奔湧而上,帶起了陣陣的溫熱,淹沒了我的臉頰。而他卻彷彿是帶有著蠟質的傾斜葉片,雨水落在它身上的瞬間會輕快地滑落,葉片始終保有自身的完好,不吸附所有落下的事物,也不留下它們經過的痕跡。
2.
「我們就這樣一直走著,好嗎?下輩子也是。」冬夜裡,他牽著我的手。
「好啊,永遠的一天。」我將他的手牽得更緊。
我純粹的確信了那個當下,彷彿忘記了生命一再向我揭示的易逝本質,又或者,是我隱隱提前感受了「失去」——那早已進駐於內心卻刻意忽略的——因而更加渴望延長那尚未衰敗的美好。(⋯⋯而美好,它可能衰敗嗎,如果它曾經在某個當下發生——在心裡。)
我們各自擁抱著內心珍惜的記憶。
而我們珍惜的記憶來自不同的當下。我珍惜的,那漫無目的的寧靜冬夜,他早已遺忘,而他所珍惜的,夏日的奔放與鮮活,卻是我認為太恣意而想抹去的灰塵。那個夏日,他像是一個精準的掠食者飛躍而來,而我,只顧著感受在鷹般的雙眼之下,像個小動物在他銳利與強健的爪子間,順服或逃脫。也許順服或逃脫,是蒼白而年輕的生命,當下唯一的意志與方向。
3.
「從小到大,我看著美好的事物在眼前逐漸瓦解。大概是因為這樣,所以國中時對一張歷史照片特別印象深刻吧。那是一戰時的德國街道,地面上堆滿了一夕之間被貶值的貨幣,像座小山一樣,小男孩還把它當積木玩。」我說。
某日夜裡,我們聊起了過往記憶。
「我的兒時記憶是一直吞西藥,一下課就要幫爸媽顧市場裡的水果攤。」「有時一到了水果攤,卻看見爸媽不在,地面上都是砸爛的水果,我就知道爸媽又吵架了。」過往對他而言彷彿純粹是生命長河裡,某個早已逝去的微小片段,他提起時,總是不帶情緒。
「我們印象深刻的事,都和『地面』有關呢。」我笑了起來。
我像是個沒落的貴族。他則是一出生就歷經苦難。
我的童年也許曾經美好,而他的童年,也許是關於刀尖與逃跑的記憶。
他常向我提起某一次,當父母又吵架,母親倉皇逃到隔壁鄰居家的床底下躲藏,父親在追上後,就彎起身子拿刀伸進床底下狠狠揮舞。「如果我媽剛好被刀揮中了,不就變成絞肉了嗎?」他說到「絞肉」時,立刻笑了出來。苦難的一切對他而言荒誕與滑稽。
4.
他總認為我嚴肅。
雖然他也曾形容我「幽默」,而我後來才發現,我的幽默屬於文字的、概念的,並未提升為一種更深刻的,看待生命的「詼諧」。
他是詼諧的人。因為痛苦養成的詼諧。而除了聲音嘶啞,以及腸胃過於敏感以外,現在的他,幾乎讓人看不到曾經受苦的影子。於是我經常想躍入,他剛來到世界上,而我還不存在的那個時空。他的身體,一定像新生的幼鼠般瘦小而脆弱,在路邊的陽光下粉紅透明,而他的額頭因為發育不全,呈奇異的階梯狀。
一個不被認為會活著的生命。從不小心滑落到這個世界,就被母親包裹在製壞了的被胎裡擱著,而遺忘了的生命。母親忍著身體的創痛,為了維繫生存而繼續在棉被廠裡工作,而拋於視線之外的,生命。過了一夜,當母親再次想起他時,以為他早已奄奄一息,沒想到,他仍在棉被裡安好地呼吸,彷彿被一股無形而溫柔的力量保護著。
*
「我經常覺得,我是不想要來到人世間,所以自己想被流產的。」這句話經常出現在他口中。
「有可能喔。你在被懷胎的時候,發現弄錯了,這不是你想要來的地方。你不想要出生,那怎麼辦?所以只好快速地出生,就可以快速地離開。」我說。
「可是我竟然活下來了,呵呵。」他的笑意味深長。
我經常思索著那一刻,維繫著他的生命並延續到此刻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