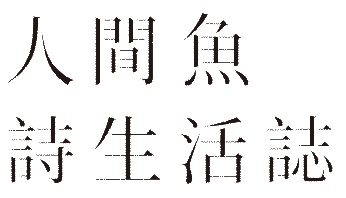無名老詩人的死前生活
文|許丁江
離不開閣樓的許家這一丁
國內新增34,358例COVID-19確定病例,分別為34,126例本土個案及232例境外移入;另確診個案中新增35例死亡。
以上是滑了手機,得知軒嵐諾這忽瘦忽胖可中可強的颱風走的那天衛福部報的昨天確診數字。我當然還是在我閣樓裡和颱風共感同在。很交響樂的兩天。我明明可下到有公媽神祖牌位的沙發客廳當顆馬鈴薯的,我是說守著電視知道台灣甚至印太怎麼了。但不想。
關於蔡英文和習近平也是我老人生命中目前重要的關鍵人物。這兩位左右著未來歷史的走向和這個世界。事實上,我也可以不重視,就人肉鹹鹹,我許家只剩我這一丁,未婚的不傳煙火的一丁,江江江江⋯⋯
滑手機的今天,從窗口望出窗外陽光普照,普照在所有的紅色層疊屋瓦上。我打開一門三窗,通風通風,也邀請陽光進來,看著我的大鐵床加那一長條桌,桌上的一長條書,往上是別人家原來開的窗,自從我媽架了這鐵皮屋以後,鄰居識趣的緊閉這窗,我就利用這窗凹進去的窗欞,弄了四層有餘的書架。我常坐在長條桌前讀書,當然不是教科書,舞文弄墨,到處舞文弄墨,最規矩的也就是在綠色稿紙上塗鴉,有時候還真的會畫一隻鴨,當寫不出什麼感覺時。對了!我要說的是坐下的我的身後便是一扇窗,窗下就是小鎮傳說中的有懸吊紅衣女鬼的公廁。我常看看書轉過身來居高臨下看著這公廁的小屋頂,也是紅瓦片的,不過有洞且漆黑,你說臭嗎?當然不臭,因為自有這傳說以來,公廁早就沒人上門了。我只知道是個老茅坑,從小到大,經過也沒想進去用用。但公所也從來沒想拆掉它。我今年都六十五了,而它比我早「出」生。
我若從長書桌走出來往閣樓門外走,便上了我晾衣服的小陽台,再往前是兩進(兩爿或兩脊)我家的紅色屋瓦,層疊的瓦海,貓、鴿子走過飛過,星星、月亮、太陽、風雨來臨是很正常的。
(年老只會重複講這些重複講過的事,腦中生命中再也沒有新增的人事了。抱歉!)
(重點是也沒有新增的物!我這輩子絲毫沒有什麼購買欲,包括使用金錢的慾望,但我不是守財奴,也沒有財之一物可守。)
我站在或坐落小陽台上抽根煙,往右邊看,掠過四棟或高或低的房子,便可看見陳冬陽家三層樓高的房子,而他年輕時的書房在二樓。(只是現在堆那麼多雜物,這還算不算是書房來著?)有時候,他也會星星之火的往我這邊斜昵一下,我們便抬抬手意思意思照會一下。我看向我家兩進的瓦海,他看向他家眼前的空闊的天空,這一照會剛好是互為一正一反。
自然這是從年輕到老的習慣了,從十七歲起。第一口煙還是他在學校廁所裡遞給我的,彼此就擱在隔板上,一口一口的,很生猛的同夥犯罪感,(應該說是他忽然很娘炮的找我一起上廁所,我覺得他怎麼⋯⋯,但還是不置可否的跟進去了。他使個眼神,意思是你一間我一間,突然聞到燒焦味,他手接下⋯⋯,總之第一次)踩這世間的邊界,爽啦!
我已經忘了,那時有沒有人把風?總之一顆心臟很刺激的跑馬拉松!
我這一生,怎可以就這樣過了
從來抽菸就不是我的強項。就抽假菸,沒真的吸吞下去,在口鼻間就讓它過出去。從來抽菸就是我的儀式性行為,一種證明我寂寞我存在的儀式嗎?不知道。再說現在抽菸的人相對少了。我們年輕時候,抽菸的人相對的多。戒嚴時代的苦悶嗎?也不知道。
常常我習慣點著一根煙夾在食指中指間。抽不到幾口,那星星之火生息生滅著⋯⋯
我這一生,怎可以就這樣過了?怎麼不可以?少廢話!多讀幾本書去吧!讀?還不是記不住什麼?跟抽假菸一樣,過一下就噴出去了。儀式性行為。如果生命都留不住什麼了,(如果個屁!生命能留住什麼?不就一堆流逝的現象?你真相信有個生命本身的什麼鬼或者認知嗎?拍謝!認知有用嗎?也不過是生滅的。)那麼多的生命,戈巴契夫不是九十一歲剛走嗎?有人說他很偉大,在共黨國家領袖裡,普丁、習近平,甚至毛澤東都沒他的胸襟偉大!但又如何?普丁連去看他遺體都不願意,是啊!連政治算計也都是時效性的而已。人類,所有的生命,哪來永恆的什麼?
忽然想起那個報告,湖南農民運動?是吧!作者就是老毛,我記起來了,這無法無天的「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偉人。至於這報告是向誰報告的呢?懶得滑手機,但想也想得到吧!
從這又想起所謂去中化云云,相對的大中國意識,共黨中國煞有介事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什麼從三國時代起?幹他馬的!老毛還主張獨立呢!從湖南到台灣。台灣要跟「中國」有關係,真扯得上一點關係的,倒是從蔣介石開始的吧!而這「中國」還是中華民國,扯不上什麼三國時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就不相信現在這個世界還是強者全拿的歷史!
任何政權的鬼扯,跟人性沒有兩樣,要怎麼論述亦即鬼扯都行,而所謂認知就顯得鬼從鬼,扯從扯了。
在眼睛還沒白內障掉,瞎了前
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等到孟樊、楊宗翰的《台灣新詩史》,我只能跟自己說,她知道你連《台灣現代詩史》,都不曾開讀,永遠停在被她(和她鄭慧如)批評的周夢蝶那幾頁!人家當然不會再花錢買書給你。雖然她知道書是你的餘生了,在眼睛還沒白內障掉,瞎了前。
我是喜歡寫詩的,寫自己的詩, 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與其說我寫詩,不如說詩寫我,因為我從來是未知的寫,不是構思好才寫的,那不是我的慣性。因為如此,所以也就不與詩壇往來,也沒買過多少本詩集,印象最深刻的是楊喚詩集!
(可是那一本有他斜斜畫像的詩集流浪何方,我也不知道了。我一直覺得是借給陳冬陽,被他玩丟了,他一口咬定沒有,說他記憶好得很,說我那少數幾本書,他都翻過,就沒翻過有這一本,我當然知道他愛的詩人是楊牧,他並不喜歡寫多了童詩的楊喚。)
至於詩的好壞,我是不管的,因為我對它沒有任何現實目的。現實不都被我放棄掉了嗎?包括人生與人的脈絡、關係,不是嗎?所以我對文字,小到不過一兩百字的文字會有任何目的嗎?沽名釣譽嗎?我信這個,不如信仰生活本身?而生活中也只剩這個未死,將老病死的「個人」了。詩人的令譽會是我的雞血嗎?會的話,就好好打雞血吧!興奮興奮。
至於詩史,也不過是一堆文字,更多的文字,只要你能自圓其說,相對的「封閉性」一下,立論「青瓷」也就得了。清楚也就是「青瓷」,也不是不能甩的。不甩在當下,也甩在未來,從未來看現在,是更容易清楚的,所謂史,後後更勝於前前,除非論(史)者有不出世的慧眼、法眼。
(說到論(史)者要有不出世的慧眼、法眼,我看不如叫所有的老和尚去吃屎吧!真和尚不是假和尚,在胸中山水這一塊是不吃俗的,一笑!不好意思,在這裡,我只想這麼說,沒什麼道理,也沒想說清楚。就一口氣罷了。)
我如果說詩史是一朝風月,而文字也不過是碎裂的泡沫,自有它與它的幸與不幸呢?
像我在我的發表場域——抽屜——有千把首詩,有寫完沒寫完的,等我屍體被公所處理掉時,除了這房子、剩下的錢的數字充公外,這些抽屜裡的詩應該是不值一顧的廢棄物吧!這就是它的不幸!
至於你,喔!至於我,為什麼不出版一冊詩集呢?我在想這是我一忽兒跑出來的情緒感覺,某種武斷的認知,值得別人再花一番時間能量來消化吸收嗎?我自己是不會不消多看自己一眼的,只此當下!
而且我的詩在她眼中是不友善的,也就是閱讀起來並不會帶來喜悅的能量。她說裡頭有太多質疑,要人沉思的東西了。
連愛我,至少對我曾有興趣的人都這樣說了。我創造自己的實相,不友善的存在,就讓它是被廢棄的吧!那些文字與這個人。
我曾經擁有她的一本筆記本
我曾經擁有她的一本筆記本,在還「超超木木」朝朝暮暮時,她有次從包包裡拿出來,「你看!這是我從國中到出社會第一年寫的東西。有些是讀閒書摘要出來的。」
她兩眼睜大發亮,眼睫毛也一根根閃著水光,至於眼眶底下的那一排也叫眼睫毛嗎?我不知道。
她遞過來要跟我分享的筆記本,是真皮的。一股體香也通透過來,順著黑糖拿鐵。我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不下踩世間邊界的那一次,但這次我有廣大的覺知把風,馬上收攝生物性能量。
假裝進入她的,世界,所思所想。我首先看到的是很流動又清秀的鋼筆字。以我們的年齡差距,不同世代,我竟然會看見鋼筆字。
都會女性不管自覺不自覺,都在嘗試或者說淬煉自己的市場價值。
「這是妳在天龍國讀書或上班時,寫的吧?」
「這時候,這個小台灣大世界還真有城鄉差距嗎?老人家。」
喔!我也不知道。
「什麼是妳的市場價值?」我當然知道她說的,但故意要問。
「就供需原理、機制,我有什麼,別人要什麼,合計合計⋯⋯」
「關係也做買賣嗎?」
「現實底層是,底層邏輯。」
「妳很敢說嘛!」
「直到遇到你這老人家,我在你的執拗裡,執拗的放棄裡,可能也是一種放下吧?我看見⋯⋯」
(我沒就這與她繼續討論下去,因為我不需要被任何人一時一地的了解。我自以為啦!)
戀愛而不進入婚姻,婚姻而不生養小孩,似乎是未來我輩必然的命運。
我深深的看著她,眼眶底下的那一排,我似乎只敢摸摸她長長的髮尾⋯⋯
「它們有分岔嗎?」
「沒。」
常常我開車在陽明大道上,趁夜,聞那一股硫磺味,尤其夜雨過後,有時候我需要速度,不只味道。起碼可以甩尾寂寞。
「幹嘛一個人?台北我知道很有些男孩不錯。」
「交往過,比較多的辦公室戀情。他們也都對我好,其實我是知道我的市場價值的,能與不能⋯⋯」
「那為什麼不走下去?」
「曾想走下去。因為我的頭腦很清楚,它永遠都不會昏睡,可是我的性格如火又很濃烈,敗的是我的身子並不想很長久的活下去⋯⋯」
我在筆記本裡,看到這個什麼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來的認知或者意志,或者男女之間,甚至男男、女女之間不用說出口的「什麼」?妳知道這是什麼嗎?我在她的筆記本裡,看到這個什麼⋯⋯
行的話,你征服我,不行的話,讓我征服你。兩性關係要嘛,就讓我心悅於你,臣服於你,請你十足強勢讓我跟從於你;要嘛,就讓我予取予求,率性並且任性而為,我的男人。
「這一則,是妳真正的想法嗎?還是寫爽的?抒發一下罷了?」
「你害怕嗎?」
這話題,我沒繼續接下去。我害怕嗎?我怕。
「放心!我活不了那麼久。」
「妳要願意活下去,這些妳都會關照和觀照的?」
「你不是說周夢蝶跟個南懷瑾?你沒跟誰?也不在意死生嗎?」
是啊!這樣活著的我怎麼會在意生死呢?但奇怪的是,人不是與生俱來就會看到或知道自己念頭的嗎?思想內容?這有很難嗎?這就要歸於佛教或者佛法嗎?
是啊!我是不喜歡兩性之間的征服觀的,若有的話,或是任何的控制觀。這很無明也很五毒,不是嗎?誰可以把誰看小了?誰可以把自己看小了?而不認識自己,不負責呢?當然,我也可能只是在這裡大放厥詞罷了。你看我是前後矛盾的,如我的人生, 如我的言論。但如果我說,這是我的選擇呢?
很不想這樣說,所以我括弧了
國內新增24,103例COVID-19確定病例,分別為23,931例本土個案及172例境外移入;另確診個案中新增31例死亡。
從陽光普照的窗口到即將進入昏黃的嘉南平原,我又滑了一下手機,這兩天死亡的案例計六十六例。死亡從來不是人的主動選擇,即便是以生命權的觀念,除非是痛苦到一個極致⋯⋯
(很不想這樣說,所以我括弧了!事實上,這疫情是讓全世界每分每秒當下的死亡事實,尤其是因為疫情而來的死亡而被數字加總報導了。然後人們會因為病毒或瘟疫的常態化,而不在乎了。麻木的接受了這日常的生活。所謂文明,所謂日常生活,所謂世界。還好有個世界末日在⋯⋯)
雖然台灣很吵很吵很無聊
今天終於來到截稿日,只好再滑滑手機,看看也再確定幾天前所敲出來的草稿。但沒辦法很專心,心情怪怪的不大悦樂。至於為什麼?不太想探討,就算了。這時候,竟跑出來一條消息:
半強迫學生參加蔣萬安的演講
戒嚴的幽靈還發生在世新大學
哈哈!猛的一笑。我忽然為台灣的無奇不有,感到莫名的快樂。這參加台北首都市長選舉的不只國民黨的蔣萬安,(連他的小旗子上都印上他阿公常見的頭像,招揚他是)蔣經國的孫子;還有柯文哲提拔的黃珊珊,至於她的黨籍不甚清楚;另外有前衛福部長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時中,號稱三腳堵。其他還有多名人士參選,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可不想查清楚,也就算了吧!
沒辦法!文章總是要結尾的,讓我說最後一句話吧。這句話是選舉再怎麼亂,總比一個人管理箝制十幾億人的腦袋好吧?雖然台灣很吵很吵很無聊⋯⋯
國內新增34,358例COVID-19確定病例,分別為34,126例本土個案及232例境外移入;另確診個案中新增35例死亡。
以上是滑了手機,得知軒嵐諾這忽瘦忽胖可中可強的颱風走的那天衛福部報的昨天確診數字。我當然還是在我閣樓裡和颱風共感同在。很交響樂的兩天。我明明可下到有公媽神祖牌位的沙發客廳當顆馬鈴薯的,我是說守著電視知道台灣甚至印太怎麼了。但不想。
關於蔡英文和習近平也是我老人生命中目前重要的關鍵人物。這兩位左右著未來歷史的走向和這個世界。事實上,我也可以不重視,就人肉鹹鹹,我許家只剩我這一丁,未婚的不傳煙火的一丁,江江江江⋯⋯
滑手機的今天,從窗口望出窗外陽光普照,普照在所有的紅色層疊屋瓦上。我打開一門三窗,通風通風,也邀請陽光進來,看著我的大鐵床加那一長條桌,桌上的一長條書,往上是別人家原來開的窗,自從我媽架了這鐵皮屋以後,鄰居識趣的緊閉這窗,我就利用這窗凹進去的窗欞,弄了四層有餘的書架。我常坐在長條桌前讀書,當然不是教科書,舞文弄墨,到處舞文弄墨,最規矩的也就是在綠色稿紙上塗鴉,有時候還真的會畫一隻鴨,當寫不出什麼感覺時。對了!我要說的是坐下的我的身後便是一扇窗,窗下就是小鎮傳說中的有懸吊紅衣女鬼的公廁。我常看看書轉過身來居高臨下看著這公廁的小屋頂,也是紅瓦片的,不過有洞且漆黑,你說臭嗎?當然不臭,因為自有這傳說以來,公廁早就沒人上門了。我只知道是個老茅坑,從小到大,經過也沒想進去用用。但公所也從來沒想拆掉它。我今年都六十五了,而它比我早「出」生。
我若從長書桌走出來往閣樓門外走,便上了我晾衣服的小陽台,再往前是兩進(兩爿或兩脊)我家的紅色屋瓦,層疊的瓦海,貓、鴿子走過飛過,星星、月亮、太陽、風雨來臨是很正常的。
(年老只會重複講這些重複講過的事,腦中生命中再也沒有新增的人事了。抱歉!)
(重點是也沒有新增的物!我這輩子絲毫沒有什麼購買欲,包括使用金錢的慾望,但我不是守財奴,也沒有財之一物可守。)
我站在或坐落小陽台上抽根煙,往右邊看,掠過四棟或高或低的房子,便可看見陳冬陽家三層樓高的房子,而他年輕時的書房在二樓。(只是現在堆那麼多雜物,這還算不算是書房來著?)有時候,他也會星星之火的往我這邊斜昵一下,我們便抬抬手意思意思照會一下。我看向我家兩進的瓦海,他看向他家眼前的空闊的天空,這一照會剛好是互為一正一反。
自然這是從年輕到老的習慣了,從十七歲起。第一口煙還是他在學校廁所裡遞給我的,彼此就擱在隔板上,一口一口的,很生猛的同夥犯罪感,(應該說是他忽然很娘炮的找我一起上廁所,我覺得他怎麼⋯⋯,但還是不置可否的跟進去了。他使個眼神,意思是你一間我一間,突然聞到燒焦味,他手接下⋯⋯,總之第一次)踩這世間的邊界,爽啦!
我已經忘了,那時有沒有人把風?總之一顆心臟很刺激的跑馬拉松!
我這一生,怎可以就這樣過了
從來抽菸就不是我的強項。就抽假菸,沒真的吸吞下去,在口鼻間就讓它過出去。從來抽菸就是我的儀式性行為,一種證明我寂寞我存在的儀式嗎?不知道。再說現在抽菸的人相對少了。我們年輕時候,抽菸的人相對的多。戒嚴時代的苦悶嗎?也不知道。
常常我習慣點著一根煙夾在食指中指間。抽不到幾口,那星星之火生息生滅著⋯⋯
我這一生,怎可以就這樣過了?怎麼不可以?少廢話!多讀幾本書去吧!讀?還不是記不住什麼?跟抽假菸一樣,過一下就噴出去了。儀式性行為。如果生命都留不住什麼了,(如果個屁!生命能留住什麼?不就一堆流逝的現象?你真相信有個生命本身的什麼鬼或者認知嗎?拍謝!認知有用嗎?也不過是生滅的。)那麼多的生命,戈巴契夫不是九十一歲剛走嗎?有人說他很偉大,在共黨國家領袖裡,普丁、習近平,甚至毛澤東都沒他的胸襟偉大!但又如何?普丁連去看他遺體都不願意,是啊!連政治算計也都是時效性的而已。人類,所有的生命,哪來永恆的什麼?
忽然想起那個報告,湖南農民運動?是吧!作者就是老毛,我記起來了,這無法無天的「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偉人。至於這報告是向誰報告的呢?懶得滑手機,但想也想得到吧!
從這又想起所謂去中化云云,相對的大中國意識,共黨中國煞有介事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什麼從三國時代起?幹他馬的!老毛還主張獨立呢!從湖南到台灣。台灣要跟「中國」有關係,真扯得上一點關係的,倒是從蔣介石開始的吧!而這「中國」還是中華民國,扯不上什麼三國時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就不相信現在這個世界還是強者全拿的歷史!
任何政權的鬼扯,跟人性沒有兩樣,要怎麼論述亦即鬼扯都行,而所謂認知就顯得鬼從鬼,扯從扯了。
在眼睛還沒白內障掉,瞎了前
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等到孟樊、楊宗翰的《台灣新詩史》,我只能跟自己說,她知道你連《台灣現代詩史》,都不曾開讀,永遠停在被她(和她鄭慧如)批評的周夢蝶那幾頁!人家當然不會再花錢買書給你。雖然她知道書是你的餘生了,在眼睛還沒白內障掉,瞎了前。
我是喜歡寫詩的,寫自己的詩, 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與其說我寫詩,不如說詩寫我,因為我從來是未知的寫,不是構思好才寫的,那不是我的慣性。因為如此,所以也就不與詩壇往來,也沒買過多少本詩集,印象最深刻的是楊喚詩集!
(可是那一本有他斜斜畫像的詩集流浪何方,我也不知道了。我一直覺得是借給陳冬陽,被他玩丟了,他一口咬定沒有,說他記憶好得很,說我那少數幾本書,他都翻過,就沒翻過有這一本,我當然知道他愛的詩人是楊牧,他並不喜歡寫多了童詩的楊喚。)
至於詩的好壞,我是不管的,因為我對它沒有任何現實目的。現實不都被我放棄掉了嗎?包括人生與人的脈絡、關係,不是嗎?所以我對文字,小到不過一兩百字的文字會有任何目的嗎?沽名釣譽嗎?我信這個,不如信仰生活本身?而生活中也只剩這個未死,將老病死的「個人」了。詩人的令譽會是我的雞血嗎?會的話,就好好打雞血吧!興奮興奮。
至於詩史,也不過是一堆文字,更多的文字,只要你能自圓其說,相對的「封閉性」一下,立論「青瓷」也就得了。清楚也就是「青瓷」,也不是不能甩的。不甩在當下,也甩在未來,從未來看現在,是更容易清楚的,所謂史,後後更勝於前前,除非論(史)者有不出世的慧眼、法眼。
(說到論(史)者要有不出世的慧眼、法眼,我看不如叫所有的老和尚去吃屎吧!真和尚不是假和尚,在胸中山水這一塊是不吃俗的,一笑!不好意思,在這裡,我只想這麼說,沒什麼道理,也沒想說清楚。就一口氣罷了。)
我如果說詩史是一朝風月,而文字也不過是碎裂的泡沫,自有它與它的幸與不幸呢?
像我在我的發表場域——抽屜——有千把首詩,有寫完沒寫完的,等我屍體被公所處理掉時,除了這房子、剩下的錢的數字充公外,這些抽屜裡的詩應該是不值一顧的廢棄物吧!這就是它的不幸!
至於你,喔!至於我,為什麼不出版一冊詩集呢?我在想這是我一忽兒跑出來的情緒感覺,某種武斷的認知,值得別人再花一番時間能量來消化吸收嗎?我自己是不會不消多看自己一眼的,只此當下!
而且我的詩在她眼中是不友善的,也就是閱讀起來並不會帶來喜悅的能量。她說裡頭有太多質疑,要人沉思的東西了。
連愛我,至少對我曾有興趣的人都這樣說了。我創造自己的實相,不友善的存在,就讓它是被廢棄的吧!那些文字與這個人。
我曾經擁有她的一本筆記本
我曾經擁有她的一本筆記本,在還「超超木木」朝朝暮暮時,她有次從包包裡拿出來,「你看!這是我從國中到出社會第一年寫的東西。有些是讀閒書摘要出來的。」
她兩眼睜大發亮,眼睫毛也一根根閃著水光,至於眼眶底下的那一排也叫眼睫毛嗎?我不知道。
她遞過來要跟我分享的筆記本,是真皮的。一股體香也通透過來,順著黑糖拿鐵。我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不下踩世間邊界的那一次,但這次我有廣大的覺知把風,馬上收攝生物性能量。
假裝進入她的,世界,所思所想。我首先看到的是很流動又清秀的鋼筆字。以我們的年齡差距,不同世代,我竟然會看見鋼筆字。
都會女性不管自覺不自覺,都在嘗試或者說淬煉自己的市場價值。
「這是妳在天龍國讀書或上班時,寫的吧?」
「這時候,這個小台灣大世界還真有城鄉差距嗎?老人家。」
喔!我也不知道。
「什麼是妳的市場價值?」我當然知道她說的,但故意要問。
「就供需原理、機制,我有什麼,別人要什麼,合計合計⋯⋯」
「關係也做買賣嗎?」
「現實底層是,底層邏輯。」
「妳很敢說嘛!」
「直到遇到你這老人家,我在你的執拗裡,執拗的放棄裡,可能也是一種放下吧?我看見⋯⋯」
(我沒就這與她繼續討論下去,因為我不需要被任何人一時一地的了解。我自以為啦!)
戀愛而不進入婚姻,婚姻而不生養小孩,似乎是未來我輩必然的命運。
我深深的看著她,眼眶底下的那一排,我似乎只敢摸摸她長長的髮尾⋯⋯
「它們有分岔嗎?」
「沒。」
常常我開車在陽明大道上,趁夜,聞那一股硫磺味,尤其夜雨過後,有時候我需要速度,不只味道。起碼可以甩尾寂寞。
「幹嘛一個人?台北我知道很有些男孩不錯。」
「交往過,比較多的辦公室戀情。他們也都對我好,其實我是知道我的市場價值的,能與不能⋯⋯」
「那為什麼不走下去?」
「曾想走下去。因為我的頭腦很清楚,它永遠都不會昏睡,可是我的性格如火又很濃烈,敗的是我的身子並不想很長久的活下去⋯⋯」
我在筆記本裡,看到這個什麼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來的認知或者意志,或者男女之間,甚至男男、女女之間不用說出口的「什麼」?妳知道這是什麼嗎?我在她的筆記本裡,看到這個什麼⋯⋯
行的話,你征服我,不行的話,讓我征服你。兩性關係要嘛,就讓我心悅於你,臣服於你,請你十足強勢讓我跟從於你;要嘛,就讓我予取予求,率性並且任性而為,我的男人。
「這一則,是妳真正的想法嗎?還是寫爽的?抒發一下罷了?」
「你害怕嗎?」
這話題,我沒繼續接下去。我害怕嗎?我怕。
「放心!我活不了那麼久。」
「妳要願意活下去,這些妳都會關照和觀照的?」
「你不是說周夢蝶跟個南懷瑾?你沒跟誰?也不在意死生嗎?」
是啊!這樣活著的我怎麼會在意生死呢?但奇怪的是,人不是與生俱來就會看到或知道自己念頭的嗎?思想內容?這有很難嗎?這就要歸於佛教或者佛法嗎?
是啊!我是不喜歡兩性之間的征服觀的,若有的話,或是任何的控制觀。這很無明也很五毒,不是嗎?誰可以把誰看小了?誰可以把自己看小了?而不認識自己,不負責呢?當然,我也可能只是在這裡大放厥詞罷了。你看我是前後矛盾的,如我的人生, 如我的言論。但如果我說,這是我的選擇呢?
很不想這樣說,所以我括弧了
國內新增24,103例COVID-19確定病例,分別為23,931例本土個案及172例境外移入;另確診個案中新增31例死亡。
從陽光普照的窗口到即將進入昏黃的嘉南平原,我又滑了一下手機,這兩天死亡的案例計六十六例。死亡從來不是人的主動選擇,即便是以生命權的觀念,除非是痛苦到一個極致⋯⋯
(很不想這樣說,所以我括弧了!事實上,這疫情是讓全世界每分每秒當下的死亡事實,尤其是因為疫情而來的死亡而被數字加總報導了。然後人們會因為病毒或瘟疫的常態化,而不在乎了。麻木的接受了這日常的生活。所謂文明,所謂日常生活,所謂世界。還好有個世界末日在⋯⋯)
雖然台灣很吵很吵很無聊
今天終於來到截稿日,只好再滑滑手機,看看也再確定幾天前所敲出來的草稿。但沒辦法很專心,心情怪怪的不大悦樂。至於為什麼?不太想探討,就算了。這時候,竟跑出來一條消息:
半強迫學生參加蔣萬安的演講
戒嚴的幽靈還發生在世新大學
哈哈!猛的一笑。我忽然為台灣的無奇不有,感到莫名的快樂。這參加台北首都市長選舉的不只國民黨的蔣萬安,(連他的小旗子上都印上他阿公常見的頭像,招揚他是)蔣經國的孫子;還有柯文哲提拔的黃珊珊,至於她的黨籍不甚清楚;另外有前衛福部長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時中,號稱三腳堵。其他還有多名人士參選,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可不想查清楚,也就算了吧!
沒辦法!文章總是要結尾的,讓我說最後一句話吧。這句話是選舉再怎麼亂,總比一個人管理箝制十幾億人的腦袋好吧?雖然台灣很吵很吵很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