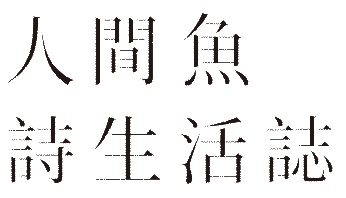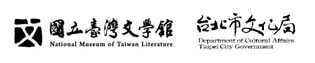評審的評審V.S作者的評審
文 離畢華
在經歷一些大大小小的獎戰之後,自己也成為評審。接受評審文學獎的任務之初,我捫心自問:以我的學養和深度,行嗎?或者主辦單位選我的原因只是豐富的參賽經驗?
參加文學賽事的文人們,各個的初發心是什麼?我的初發心是什麼?當時,臭硬的脾氣認為自己的文章不論好壞都不用旁人置喙,因為只有自己最能明瞭自己作品的長短深淺。弔詭的是,在充足的自信裡面有許多盲點,這些盲點只有旁觀者清楚,因此,你必須請教他人,以客觀甚或容許主觀的角度來評論。
當然論者必須對為文作詩有一定高度的常識/知識,試舉一例,現今流行台語文,找來的評者不能口說手寫的操作台語文、不識台語文之美之妙,更反而覺得台語文讀來聱牙佶屈,那,他能評出好的台語文作品嗎?(拙作《十三暝的月最美》吃的就是這個虧。)更有甚者,坐在我身邊的女性評審開口第一句話是,「最近很忙,所以我今天要來之前才讀了各位的作品……」,真真讓人吃驚,吃驚於她公然對每一位參賽作者以及作品的藐視。這款評審真該被評審一番。
第二,名次的決定大多以多數決為定,這看似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性」決議,真能決定文字、文化甚至文明的優劣嗎?譬如三個評審理遇上其中A、B兩個繡花枕頭的評審,以投票票數論結果,另一位真正學養均佳的C評審即便和他們據理力爭的辯論得口乾舌燥待又奈何?或者有一位A評審因口才便給且盛名蓋世,其他B、C兩位無法力爭到底,結果B懾於其聲勢而改變己見,輾壓了C的真知灼見,主持人又適時地推進到投票表決的階段(其實他/她眼看著即將下班而趕急),因此名次決定,這樣得出來的名次是客觀的嗎?君不見最近幾次的著名獎項的作品,都只蹭到臉書層級的高度而大受撻伐,不是嗎?這樣的結果,評審也有大部分的責任。
如果把歷屆各類得獎作品攤在一塊來看,不難發現近十年來,「附註」有喧賓奪主之勢。文末附註的原本用意只在於註名出處、專業名詞(尤其是外文、外來語)的解說、關於文本來龍去脈的簡略交代或註明而已。可是最近現象,可能是作者擔心評審不懂文意以致「被遺珠」,於是卯起來註一註二註三一路註下去。等而下之者更大抄史料,而評審看了文末「史料」果然可以不費心神腦力清楚明瞭作者意思,於是大筆一揮,選出淺薄的、嬌柔造作的、毫無意義的、所謂「得獎體」的作品。
至於以單篇作品論高低,尤其對一個獎額超高的文學獎而言,無可諱言的是一項極大的冒險。即便以一整本的詩集來評比也必須謹慎觀之。原因在於有些寫者是爆發型的,她/他可能一輩子只出這一本為獎而寫的集子,果然得獎,而後便如旋即凋滅的煙火一般;或者只出一本而僥倖得獎抱走高額獎且浪得虛名,更是無心致力於文章一事,那主辦方不顯得像冤大頭一樣?這並未達到提升詩壇詩質、提拔優秀新手的目的。二十多年前早有識者提出「首獎(或各獎)得主有續航力嗎?」這樣的現象和質疑。如若不正視這個現象,參賽簡章上冠冕堂皇的「主旨」不過是因循苟且的侉侉之詞罷了。至於參賽篇數或本數如何制定,滾滾諸公大老必有灼見,不勞泛泛呶呶。個人淺見:高額獎金一人獨得可以,有個但書:在未來一年內必要再出版一集供主辦方提供給各詩社,各詩社再提出評論文字(主辦方支付稿費),議論公開公評,證明作者確有材資,若是佳評一片,足證得獎人才氣;否則驗證抄短線的作者不過爾爾,對他自是一個警惕;再者,也為獎金獵人設下更高門檻,以免無品的得獎者在得了幾個獎後竟然於公開演講時大放「得獎技巧/技術」之闕詞。
參加文學賽事的文人們,各個的初發心是什麼?我的初發心是什麼?當時,臭硬的脾氣認為自己的文章不論好壞都不用旁人置喙,因為只有自己最能明瞭自己作品的長短深淺。弔詭的是,在充足的自信裡面有許多盲點,這些盲點只有旁觀者清楚,因此,你必須請教他人,以客觀甚或容許主觀的角度來評論。
當然論者必須對為文作詩有一定高度的常識/知識,試舉一例,現今流行台語文,找來的評者不能口說手寫的操作台語文、不識台語文之美之妙,更反而覺得台語文讀來聱牙佶屈,那,他能評出好的台語文作品嗎?(拙作《十三暝的月最美》吃的就是這個虧。)更有甚者,坐在我身邊的女性評審開口第一句話是,「最近很忙,所以我今天要來之前才讀了各位的作品……」,真真讓人吃驚,吃驚於她公然對每一位參賽作者以及作品的藐視。這款評審真該被評審一番。
第二,名次的決定大多以多數決為定,這看似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性」決議,真能決定文字、文化甚至文明的優劣嗎?譬如三個評審理遇上其中A、B兩個繡花枕頭的評審,以投票票數論結果,另一位真正學養均佳的C評審即便和他們據理力爭的辯論得口乾舌燥待又奈何?或者有一位A評審因口才便給且盛名蓋世,其他B、C兩位無法力爭到底,結果B懾於其聲勢而改變己見,輾壓了C的真知灼見,主持人又適時地推進到投票表決的階段(其實他/她眼看著即將下班而趕急),因此名次決定,這樣得出來的名次是客觀的嗎?君不見最近幾次的著名獎項的作品,都只蹭到臉書層級的高度而大受撻伐,不是嗎?這樣的結果,評審也有大部分的責任。
如果把歷屆各類得獎作品攤在一塊來看,不難發現近十年來,「附註」有喧賓奪主之勢。文末附註的原本用意只在於註名出處、專業名詞(尤其是外文、外來語)的解說、關於文本來龍去脈的簡略交代或註明而已。可是最近現象,可能是作者擔心評審不懂文意以致「被遺珠」,於是卯起來註一註二註三一路註下去。等而下之者更大抄史料,而評審看了文末「史料」果然可以不費心神腦力清楚明瞭作者意思,於是大筆一揮,選出淺薄的、嬌柔造作的、毫無意義的、所謂「得獎體」的作品。
至於以單篇作品論高低,尤其對一個獎額超高的文學獎而言,無可諱言的是一項極大的冒險。即便以一整本的詩集來評比也必須謹慎觀之。原因在於有些寫者是爆發型的,她/他可能一輩子只出這一本為獎而寫的集子,果然得獎,而後便如旋即凋滅的煙火一般;或者只出一本而僥倖得獎抱走高額獎且浪得虛名,更是無心致力於文章一事,那主辦方不顯得像冤大頭一樣?這並未達到提升詩壇詩質、提拔優秀新手的目的。二十多年前早有識者提出「首獎(或各獎)得主有續航力嗎?」這樣的現象和質疑。如若不正視這個現象,參賽簡章上冠冕堂皇的「主旨」不過是因循苟且的侉侉之詞罷了。至於參賽篇數或本數如何制定,滾滾諸公大老必有灼見,不勞泛泛呶呶。個人淺見:高額獎金一人獨得可以,有個但書:在未來一年內必要再出版一集供主辦方提供給各詩社,各詩社再提出評論文字(主辦方支付稿費),議論公開公評,證明作者確有材資,若是佳評一片,足證得獎人才氣;否則驗證抄短線的作者不過爾爾,對他自是一個警惕;再者,也為獎金獵人設下更高門檻,以免無品的得獎者在得了幾個獎後竟然於公開演講時大放「得獎技巧/技術」之闕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