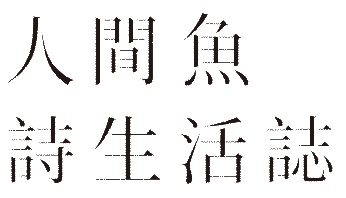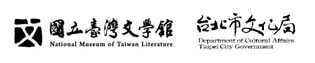詩的形式與內涵
文 楊風
大家都知道,現今流行在詩壇上的新詩或現代詩的創始人,是民國初年的胡適(1891-1962)。那是他所推動的白話文運動的最後一環。他在〈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當中,把新詩定位在新詩所用文字(白話文)的大解放。他認為,這是古今中外文學革命的共同特色;他說:
我常說,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
他舉歐洲三百年前各國的國語文學運動,從詩文必須採用拉丁文,到採用各國不同語言的大解放;例如,十八十九世紀法國囂俄(Victor Hugo,又譯雨果)、英國華次活(Wordsworth,華滋華斯)等人所提倡的文學改革,都是詩的語言文字的解放。而中國的文學革命也是如此,從古體詩發展到近體詩,從講究平仄、對仗、每句字數相同的格律詩體,到長短句還可歌唱的宋詞,再從宋詞發展到元曲,這些過程,都是胡適所說的"文的形式"大解放。
然而,卜商(孔子弟子子夏)所寫的〈毛詩序〉卻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可見,詩的核心不只是外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實質的內涵,也就是卜商所說的「志」、「情」。
胡適當然知道這個道理,因此,他在〈談新詩〉中接著說:
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
這次《人間魚詩生活誌》願意花大錢,主辦「金像獎詩人百萬賞」的徵稿,相信主辦單位所徵得的詩作,既能兼顧「文的形式」解放,也能衷心傳達詩人內心的「志」、「情」。
有些人也許還疑惑:白話詩如何進行「文的形式」解放?這當然不是要回到文言的古詩窼臼,也不是要創造現行白話之外的新語言。而是要在白話詩句裡,做一點形式的變化。早年,現代派的林亨泰,曾以圖像詩而聞名。他認為,白話詩「在文字上,即立體主義。」(見:林亨泰〈中國詩的傳統〉,刊於《現代詩》20期。)他認為,中國字的特色是空間感(立體感);這和西洋文字的特色是時間感,有所不同。他在〈中國詩的傳統〉一文中說:中國的文字,不是「音標文字」,而是依據六書原理,所構成的方塊字,因此字的本身就具有立體感。
他這個觀點,和新心理分析學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的健將──佛洛姆(Erich Fromm)的說法,相符合。佛洛姆在他的〈心理分析與禪〉一文中,曾以「下雨」(it rains)這一語句為例,說明不同民族會有不同的著重點:希伯來文注重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卻不注重時間的過程;拉丁文既注重完成式和未完成式,也注重時間的過程;英語所注重的則是時間的過程。而在中文,著重的不是時間而是空間;這從「下雨」這一詞的「下」字具有空間意義,即可明白。
中國文字既然是立體性的(空間性的),那麼像古詩詞一樣,不好好發揮它的這個特性,就太可惜了。古詩詞先是以每行字數的限定(如五言、七言),以及行數的不可更改(如絕句只能有四句),乃至對仗、平平仄仄的押韻等等嚴格的規律,來完成一首詩。宋詞和元曲也是採取相似的方法,要人把詩句填入固定的幾個「詞牌」。而元曲,儘管採用了一般平民百姓的口語,在文字的數目上,用「襯字」的方式,改變詞句的字數;但在寫作的技巧上,基本上與宋詞,同屬一類。
相對於唐詩的固定行數和字數,宋詞和元曲的「文的形式」解放是長短句;胡適提倡的白話詩,是這一解放的進一步。善用這個特色,長短句,就可成為白話詩的美學要件。中國字的特色是:每個字都是一幅(方形的)圖,因此,由圖(字)所堆疊地來的每一段(篇)詩也是一幅圖。詩中詞句的長或短,可以用來判定這幅圖的好壞;當然也會影響它是不是一篇好詩。而這些「文的形式」都是自由自在的,沒有固定的、非遵守不可的「圖庫」。
白話詩和古詩詞一樣,有「文的形式」必須照顧;但同等重要的是它的內涵,也就是卜商所說的「志」和「情」。而這卻是另一個一時難以說清楚的問題。但有一點,是目前即可說清楚的:志,必須是自己的志;情必須是自己的情。(2022/12/24)
我常說,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
他舉歐洲三百年前各國的國語文學運動,從詩文必須採用拉丁文,到採用各國不同語言的大解放;例如,十八十九世紀法國囂俄(Victor Hugo,又譯雨果)、英國華次活(Wordsworth,華滋華斯)等人所提倡的文學改革,都是詩的語言文字的解放。而中國的文學革命也是如此,從古體詩發展到近體詩,從講究平仄、對仗、每句字數相同的格律詩體,到長短句還可歌唱的宋詞,再從宋詞發展到元曲,這些過程,都是胡適所說的"文的形式"大解放。
然而,卜商(孔子弟子子夏)所寫的〈毛詩序〉卻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可見,詩的核心不只是外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實質的內涵,也就是卜商所說的「志」、「情」。
胡適當然知道這個道理,因此,他在〈談新詩〉中接著說:
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
這次《人間魚詩生活誌》願意花大錢,主辦「金像獎詩人百萬賞」的徵稿,相信主辦單位所徵得的詩作,既能兼顧「文的形式」解放,也能衷心傳達詩人內心的「志」、「情」。
有些人也許還疑惑:白話詩如何進行「文的形式」解放?這當然不是要回到文言的古詩窼臼,也不是要創造現行白話之外的新語言。而是要在白話詩句裡,做一點形式的變化。早年,現代派的林亨泰,曾以圖像詩而聞名。他認為,白話詩「在文字上,即立體主義。」(見:林亨泰〈中國詩的傳統〉,刊於《現代詩》20期。)他認為,中國字的特色是空間感(立體感);這和西洋文字的特色是時間感,有所不同。他在〈中國詩的傳統〉一文中說:中國的文字,不是「音標文字」,而是依據六書原理,所構成的方塊字,因此字的本身就具有立體感。
他這個觀點,和新心理分析學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的健將──佛洛姆(Erich Fromm)的說法,相符合。佛洛姆在他的〈心理分析與禪〉一文中,曾以「下雨」(it rains)這一語句為例,說明不同民族會有不同的著重點:希伯來文注重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卻不注重時間的過程;拉丁文既注重完成式和未完成式,也注重時間的過程;英語所注重的則是時間的過程。而在中文,著重的不是時間而是空間;這從「下雨」這一詞的「下」字具有空間意義,即可明白。
中國文字既然是立體性的(空間性的),那麼像古詩詞一樣,不好好發揮它的這個特性,就太可惜了。古詩詞先是以每行字數的限定(如五言、七言),以及行數的不可更改(如絕句只能有四句),乃至對仗、平平仄仄的押韻等等嚴格的規律,來完成一首詩。宋詞和元曲也是採取相似的方法,要人把詩句填入固定的幾個「詞牌」。而元曲,儘管採用了一般平民百姓的口語,在文字的數目上,用「襯字」的方式,改變詞句的字數;但在寫作的技巧上,基本上與宋詞,同屬一類。
相對於唐詩的固定行數和字數,宋詞和元曲的「文的形式」解放是長短句;胡適提倡的白話詩,是這一解放的進一步。善用這個特色,長短句,就可成為白話詩的美學要件。中國字的特色是:每個字都是一幅(方形的)圖,因此,由圖(字)所堆疊地來的每一段(篇)詩也是一幅圖。詩中詞句的長或短,可以用來判定這幅圖的好壞;當然也會影響它是不是一篇好詩。而這些「文的形式」都是自由自在的,沒有固定的、非遵守不可的「圖庫」。
白話詩和古詩詞一樣,有「文的形式」必須照顧;但同等重要的是它的內涵,也就是卜商所說的「志」和「情」。而這卻是另一個一時難以說清楚的問題。但有一點,是目前即可說清楚的:志,必須是自己的志;情必須是自己的情。(2022/12/24)